
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世界以及现代进程都与文化交流和翻译密不可分。中外文化交流在早期阶段主要发生在边境地区或接触区(contact zone)(范发迪 2018:3),其中长城在关口内外的附加经济功能特别重要。另外,法国汉学 家谢和耐(2010:167)还特别指出:“华南与长江流域各城市在六朝时代(222-589年)接待 愈来愈多的来自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外国人,同时华北各城市也形成外来商人区域,这些商人来自中亚绿洲以及位于锡尔河与目前印度、伊朗边界之间的地区。其中有吐鲁番人、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撒马尔罕人、布哈拉人、大夏人、白沙瓦人、东伊朗人、克什米尔人、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人等”。
由于往来人员复杂,语言混用的现象也格外突出,例如中原地区西北部除匈奴、突厥、楼兰语等语言之外,也有包括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在内等语言在宗教中心、商旅沿线、中转市镇以及关口等地区混用(Hung 2005)。在众多混杂的人员往来和商品交流中,翻译无疑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活动。这些历史性的文化交流及 翻译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一些汉学家注意到了其中翻译的作用和翻译过程的复杂性。例如莱顿大学教授许理和(2017:287)特别指出:“大多数法师抵达中国时,不懂汉语或知之甚少。……据我们所知,译经的主要工作并不是由多少已经汉化的外国僧人完成的,而是由通晓几种语言的中国人完成 的”。谢和耐(2010:232)也特别说明,“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接触并不限于佛教这一丰富多彩的领域。印度的世俗科学也深入到中国。唐代上半叶,来自印度的学者出入于长安与洛阳。7-8世纪,看来已译出大量‘婆罗门教’经文,内中涉及天文学、星相学、数学、医学等。但中国数学反过来也影响印度数学”。所 以,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中的作用也是难以替代的。而外来文化、思想指向与本土经验的结合往往会促使知识谱系的扩容与叠加。
中国古代知识谱系与其历史条件所形成的认知模式有关,其知识形态的分类主要是围绕经世致用展开的,其中包括从儒学到杂学等20余种大类。中国古代学术史在各历史时期的侧重点与其内外条件、语言及思想发展一致,即先秦诸子、汉代经学及黄老术、魏晋南北朝玄学、隋唐佛教与经学统一、宋元明理学以及清代实学等(林尹2006)。这一轨迹也包含了外来文化经由翻译与中国学术产生的结合。钱穆(2011)在其《国学概论》中就将佛经的翻译与诠释作为学术思想加以讨论,因为作为文化事件并经翻译使佛教进入中国的影响是持久的,除了语言、信仰以及叙述模式的巨大影响之外,也包括对宇宙本原的思考以及推导出实现人性圆满境界的分析方式等(葛兆光1998:552)。其次,中国对于技术类实学的引介除上述与印度的交往之外,还有西方的影响,所以谢和耐(2010: 499)对此特别加以说明:“虽然在哲学领域方面,西方影响极为零散,而且只是 在1900年左右自从译著问世之后才开始产生直接影响,但在科学技术方面,吸收情况出现得更早:曾进行漫长的比较工作,将外国成果纳入中国传统之中,其开端起码可上溯到利玛窦时代,即17世纪初”。
然而,中国囿于自身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知识谱系在近代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首先是由翻译引入的社会现代性问题,亦即经由翻译而来的“源于19 世纪欧洲思想的最为全面的‘变革的社会学’”(德里克2005:1)。中国近代史学者罗志田(2019:21)认为,“对于中国而言,那是一个不得不变革的时代,也就是一个学习的时代。近代的历史,大约就是一个在外力冲击下从被迫转变到主动改革的进程”。于是,固有认知和表达的局限迫使当时的知识界借用外来思想与话语方式。
柳诒徵(1988:798-799)对那个时期的翻译活动有明确说明,“近世译才,以侯官严复为称首。其译赫胥黎《天演论》标举译例,最中肯綮。…… 嗣译斯密亚丹之《原富》、穆勒约翰之《名学》、斯宾塞尔之《群学肄言》、孟德斯鸠之《法意》、甄克思之《社会通诠》等书,悉本信、达、雅三例,以求与晋、隋、唐、明诸译书相颉颃。于是华人始知西方哲学、计学、名学、群学、法学之深邃,非徒制造技术之轶于吾土。是为近世文化之大关键”。
概言之,中国知识界当时对西方大规模的译介形成了某种“被译介的现代性”或“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刘禾 2002:7)。一些重要著作的翻译在其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惠 顿(Wheaton)的《万国公法》(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W. Martin)汉译,由恭亲王奏折,“权力”、“主权”等词语均源自这部译著,影响很大。例如其中right一词的处理就是将中文“权势”的负面含义隐去,同时将“利”从商业语义中剥离,设置出“权利”的某种普遍性含义(刘禾2009: 163-172)。这类例子还有很多。此外,还包括英国传教士合信(B. Hobson)所著的解剖学《全体新论》(A New Theory of the Body)(1851 年在广东出版)等关于现代医学和科技的若干论著(见增田涉 2011)。
社会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翻译经济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以及西洋小说所引入的文化精神。除了重要文本的引介和翻译之外,还包括博物学,例如当时到广州的一些英国博物学者对中国植物展开的收集、命名等“文化与物质的实作”( cultural and material practice)(范发迪 2018:5)。中国特殊的海拔和气候 所拥有的动植物带也构成了近代知识探索中的重要环节。其中典型的就有19世纪到中国的法国人谭卫道(J. David)对大小熊猫以及大量动植物进行分类和命名以及19 世纪末到中国西部的英国人威尔逊(E. Wilson)对植物的考察、收集和采样等活动。当时的西方人士对收集博物采用拉丁或其他西文命名,形成了中国动植物所特有的西文学名现象。这一过程构成了近代博物学史、科学帝国主义以及特定的中西关系。这一大范围的社会现代性活动中还包括19世纪开启的公立教育、现代医学等,这些都与翻译活动交织在一起。对当时的大量译述,“梁启超制有详细的《西学书目表》(光绪二十二年序刊)”(增田涉2011: 3)分别加以说明。
由翻译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人文学术及审美现代性,包括早期利玛窦、理雅各等传教士基于语文学(philology)翻译活动所开创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潮流(见 Honey 2001)。在合力作用下,现代高等教育、学科领域以及人文学术各分支研究得以全面展开,例如语言学、文学以及翻译研究等; 其中人文学术的相关议题、理论、范畴、术语以及陈述方式等全部都与翻译活动直接相关,而现代高等教育尤为突出,“要说‘西化’,最为彻底的,也是最为成功的,当推大学教育。学科设置、课程教授、论文写作、学位评定等一环扣一环” (陈平原1998:18)。中国学术逐渐进入全球学术同一认知结构中,形成学术生 产、知识传播与审美现代性等一系列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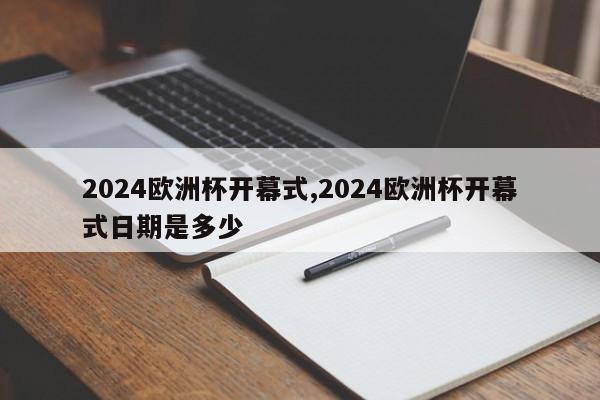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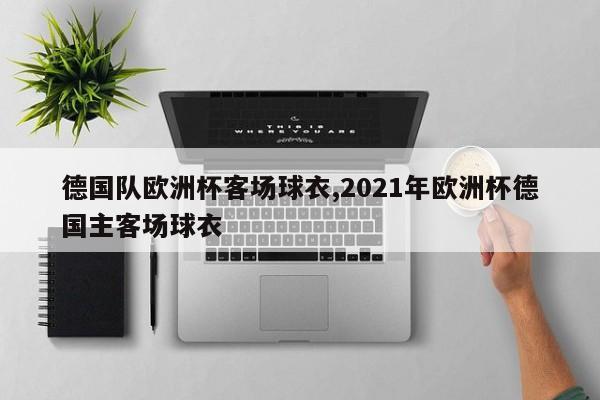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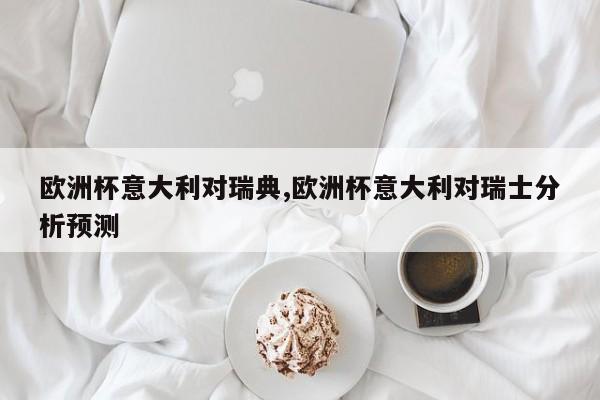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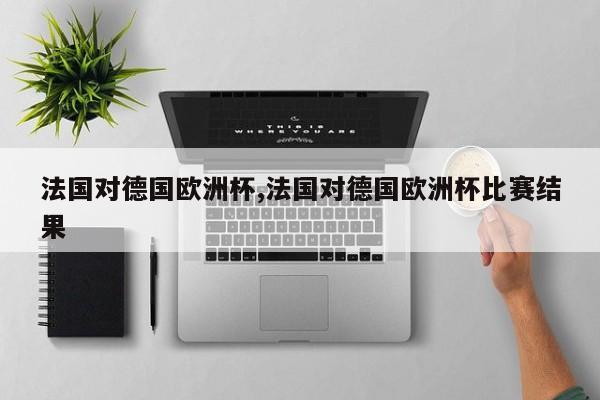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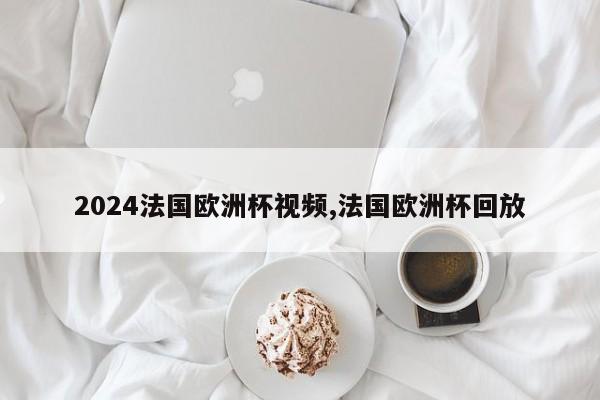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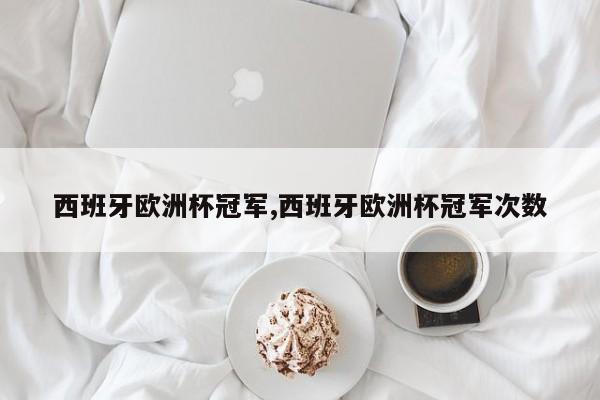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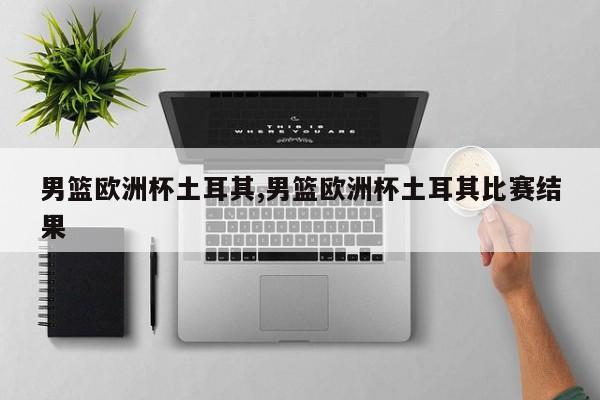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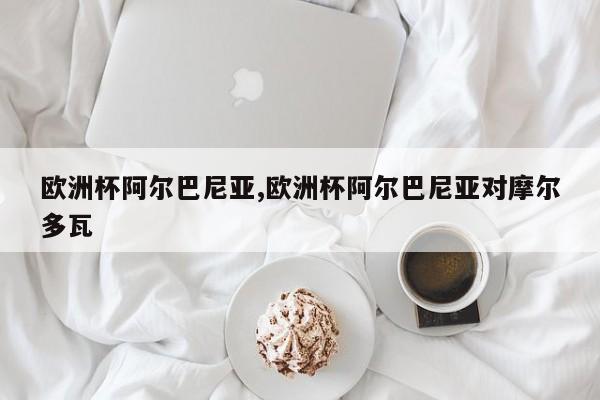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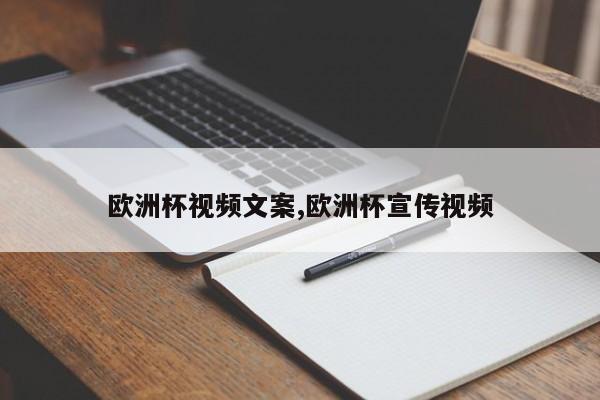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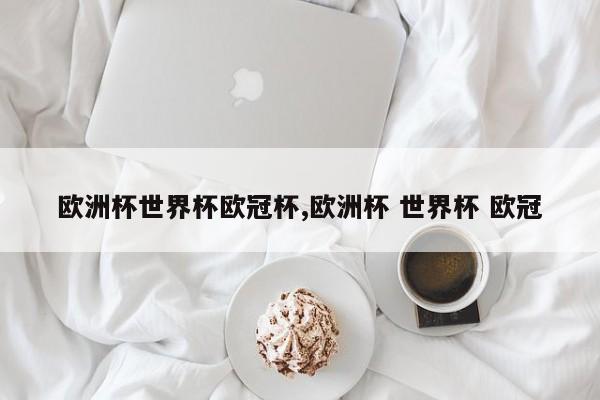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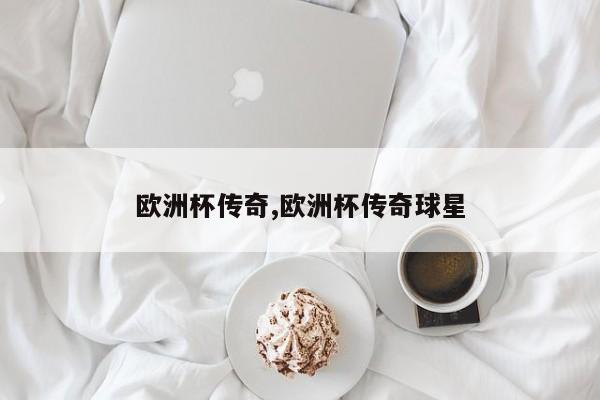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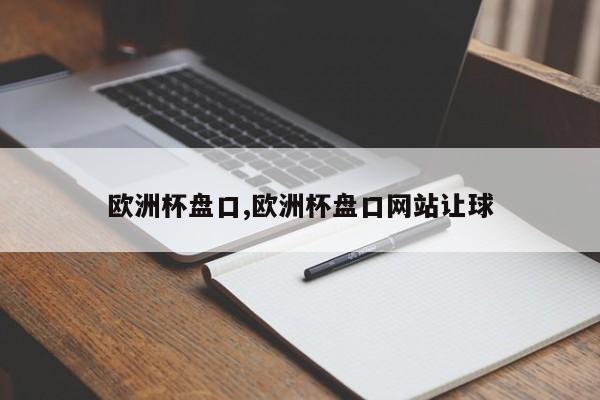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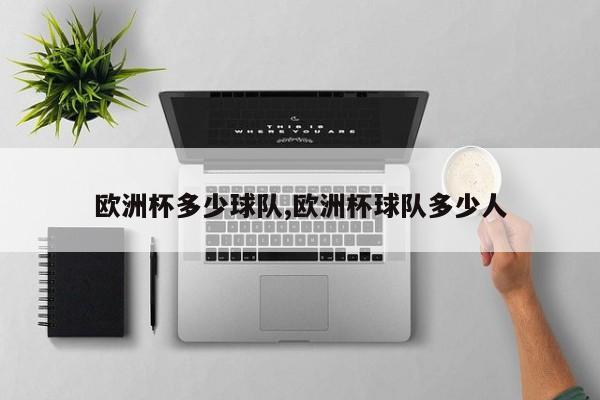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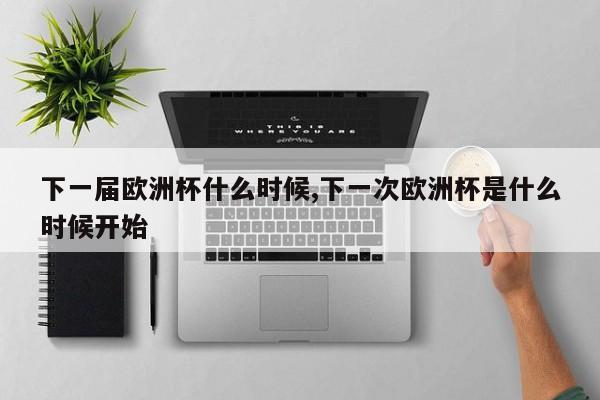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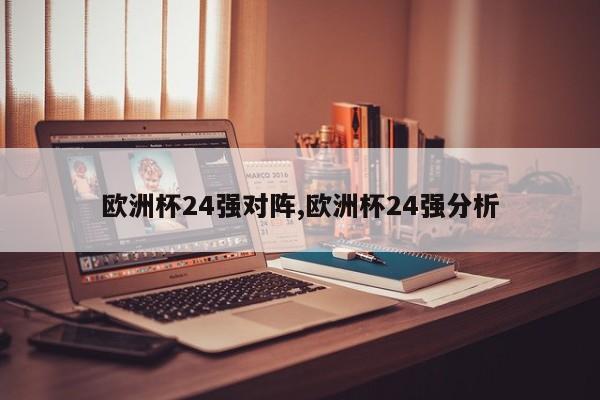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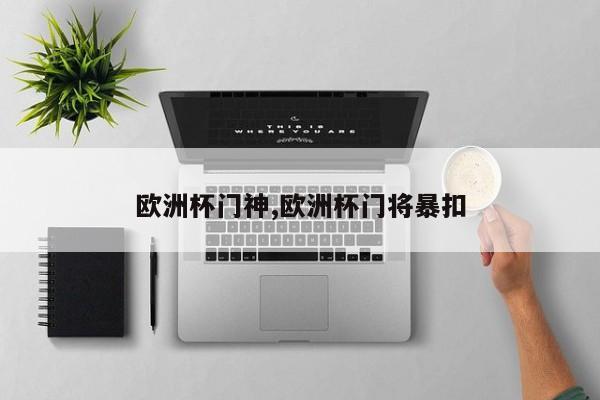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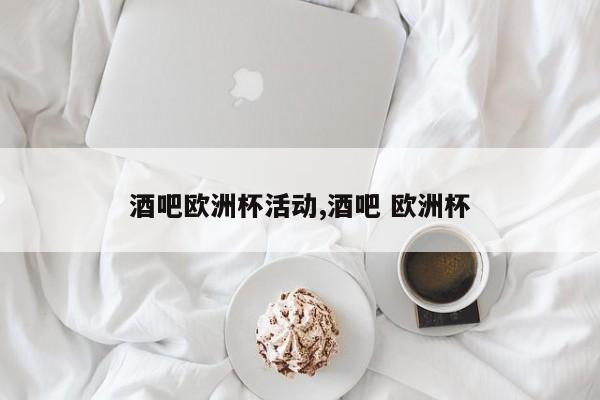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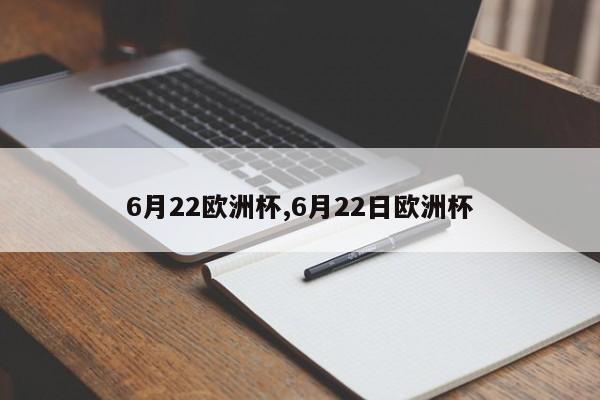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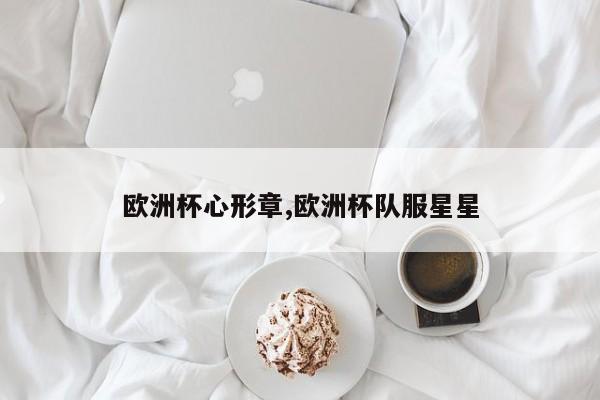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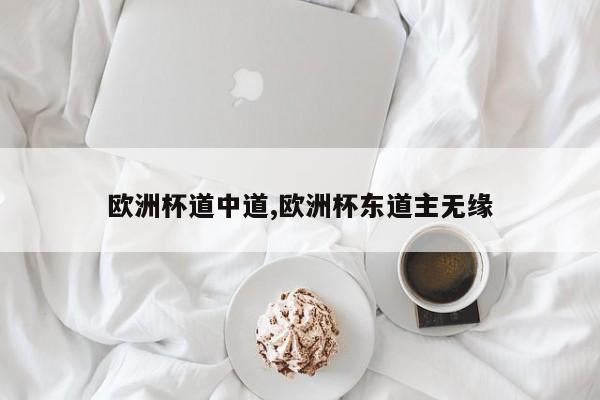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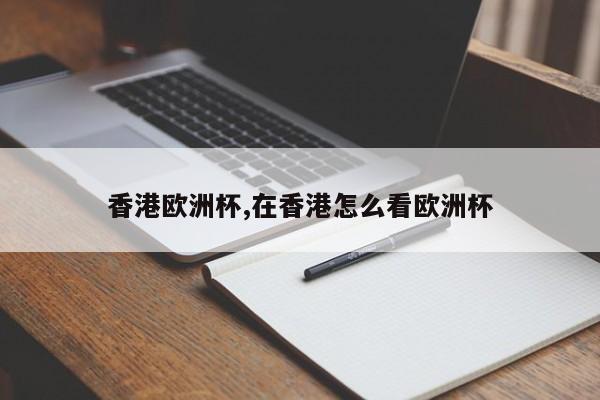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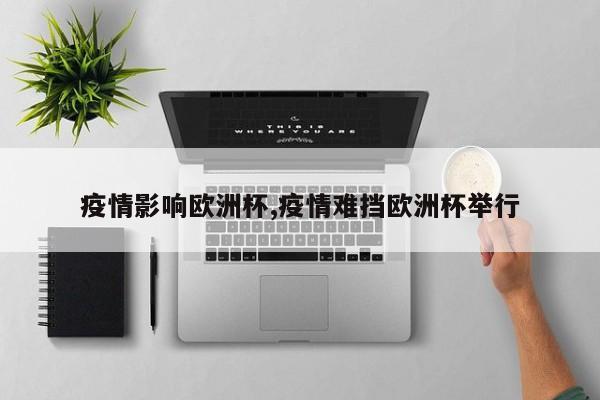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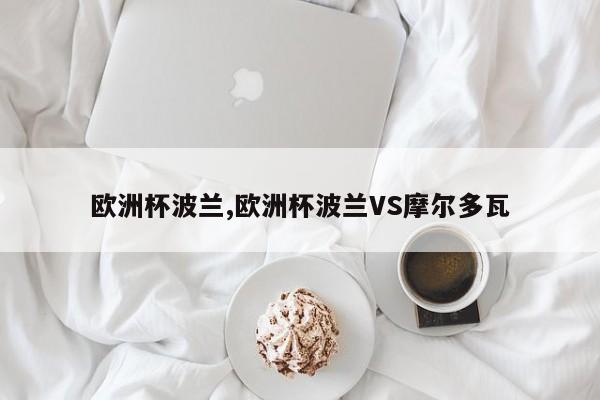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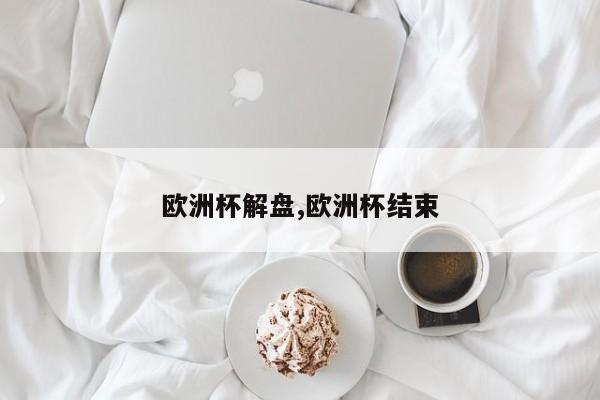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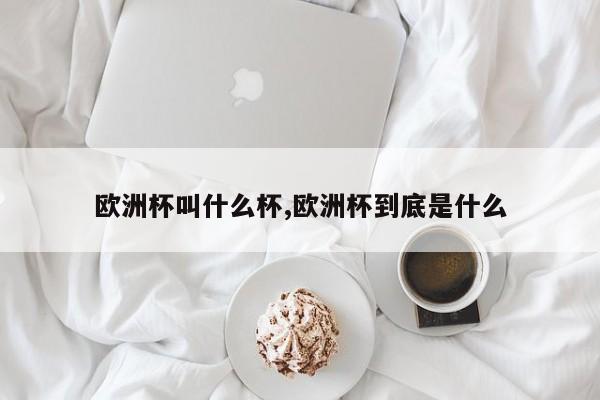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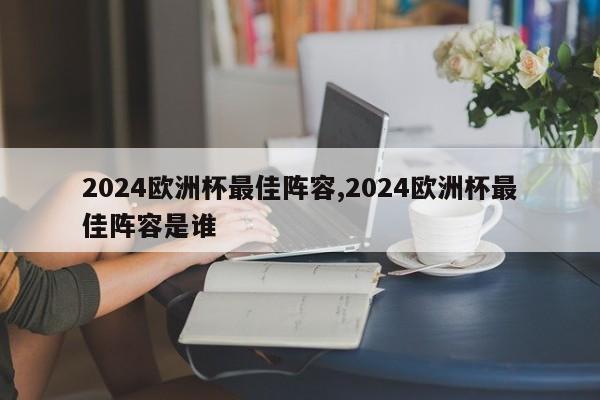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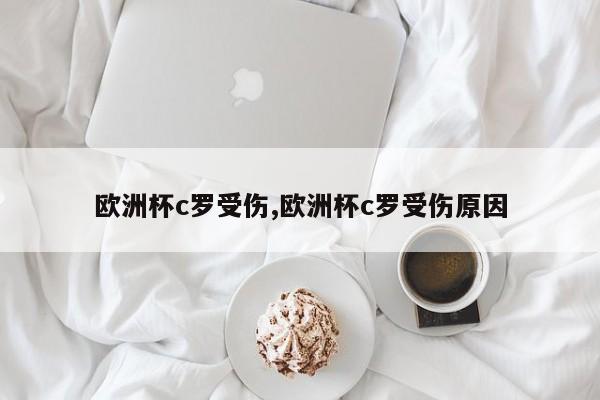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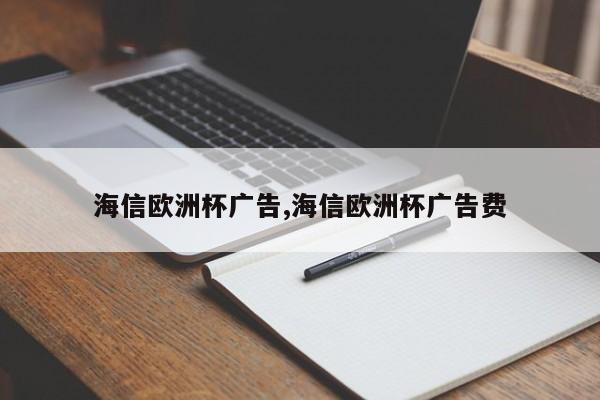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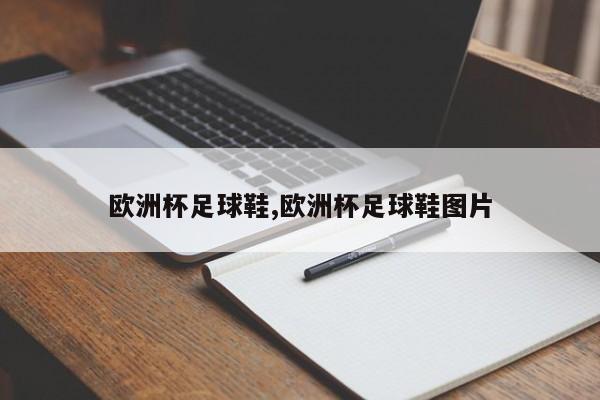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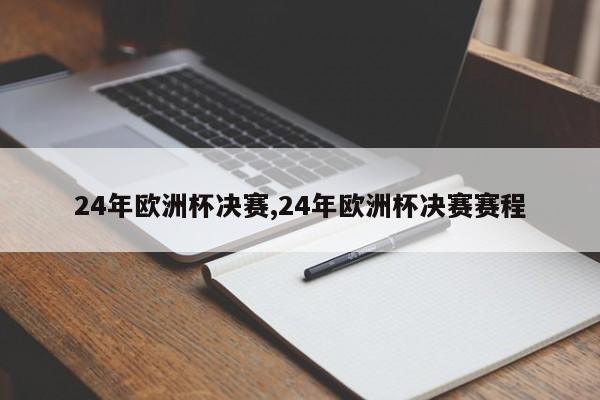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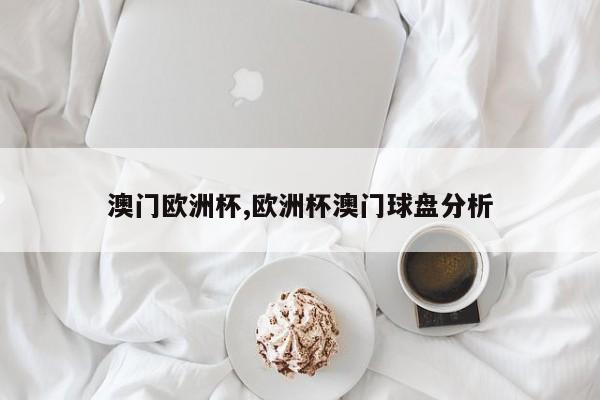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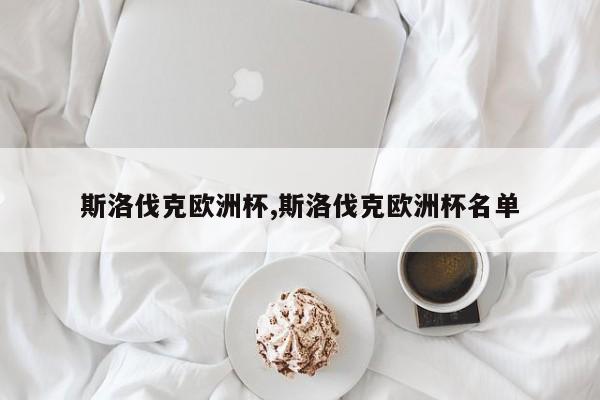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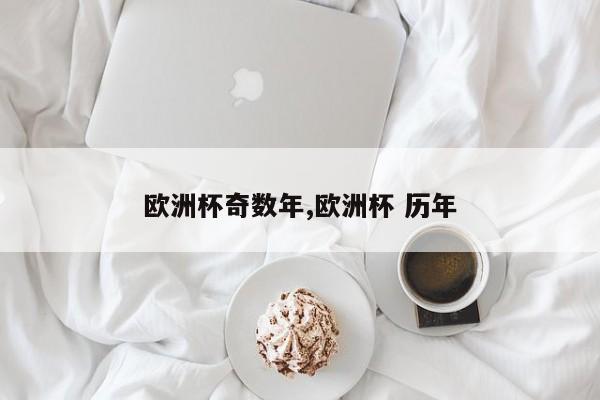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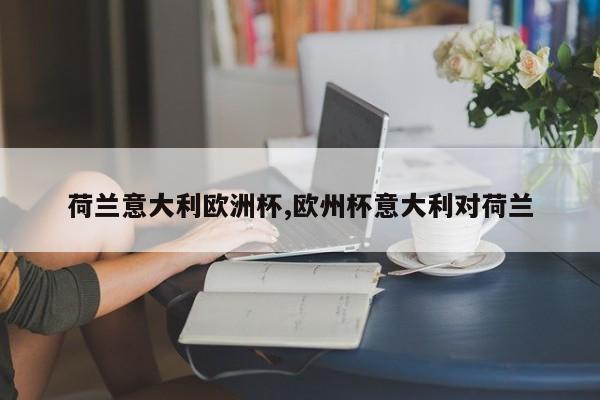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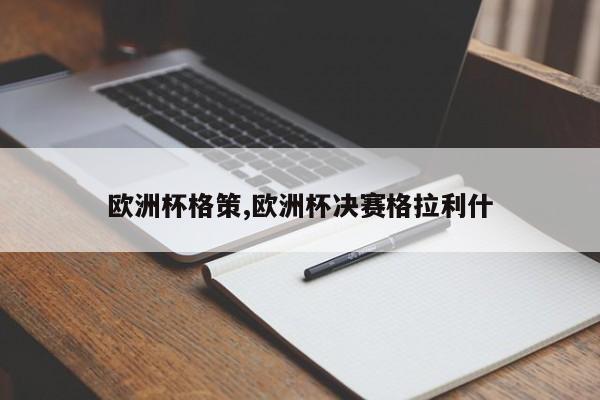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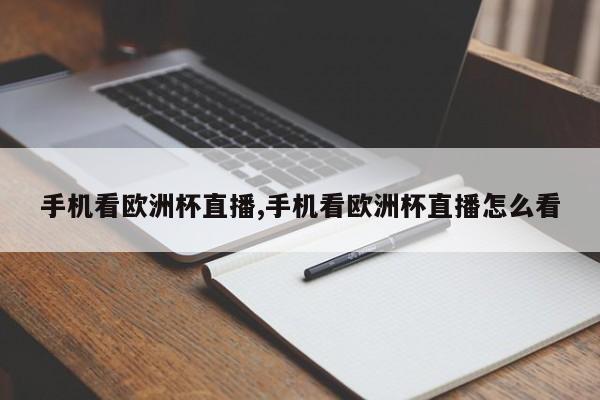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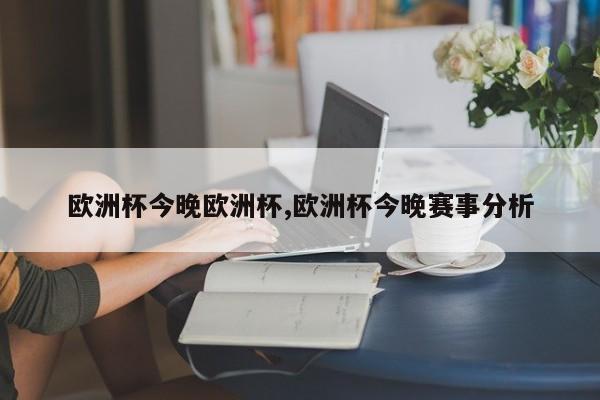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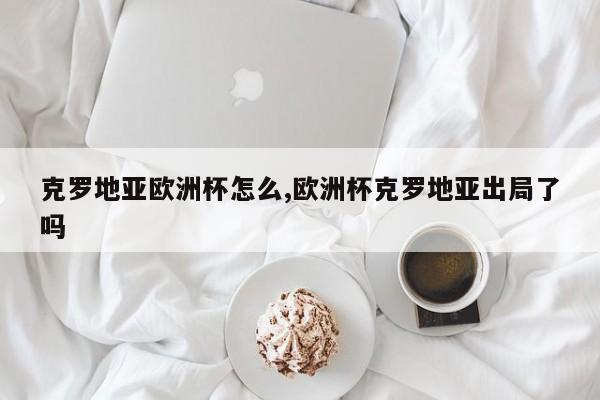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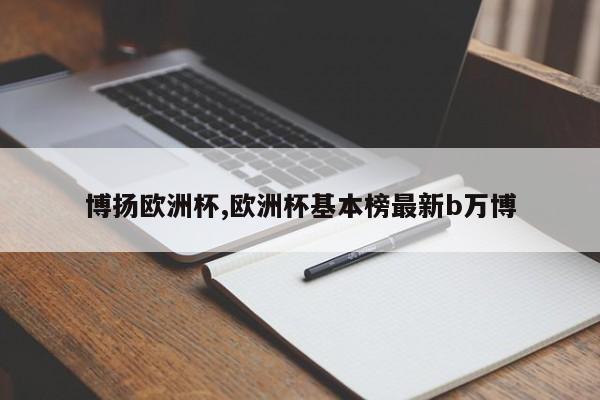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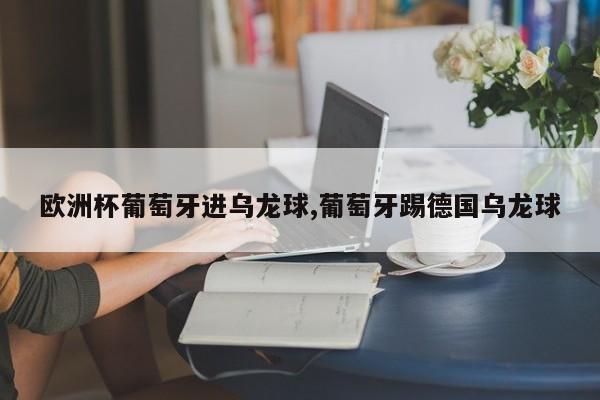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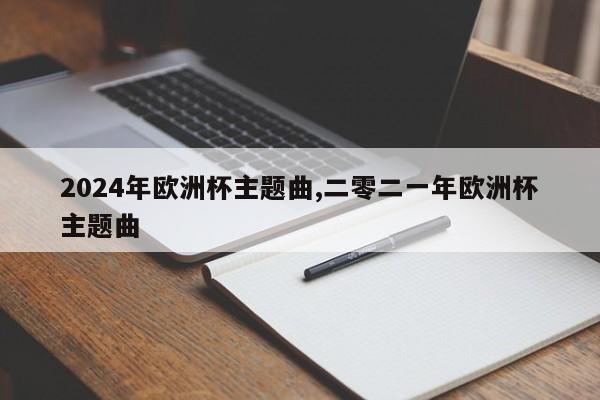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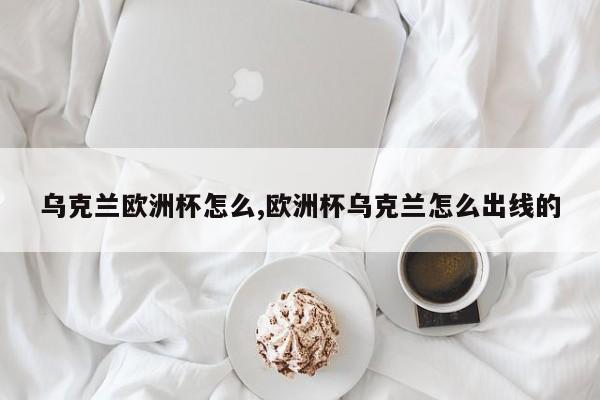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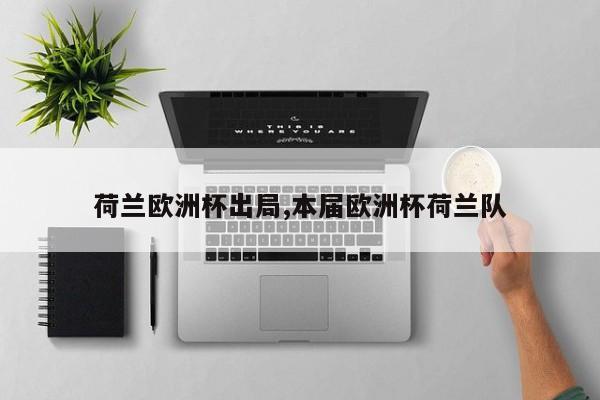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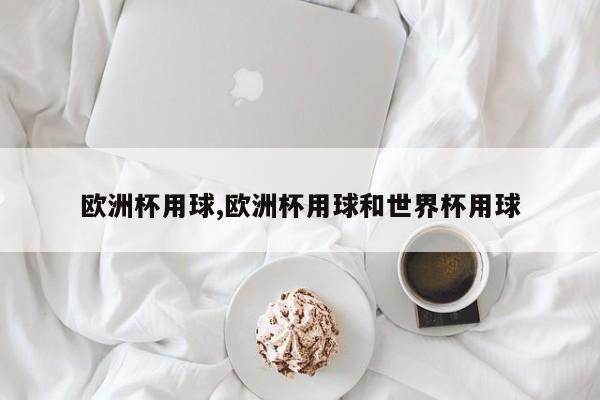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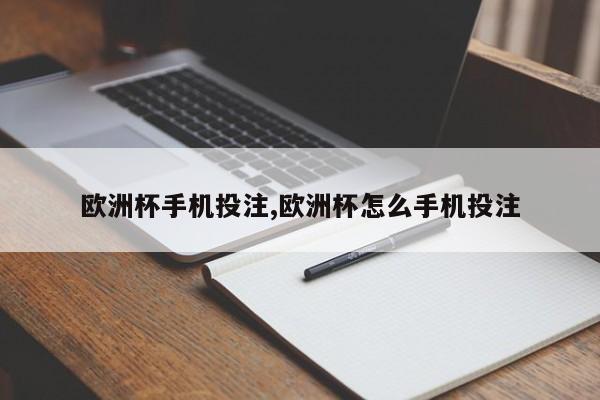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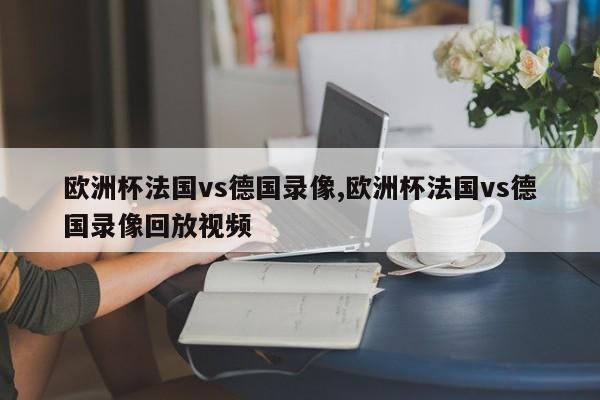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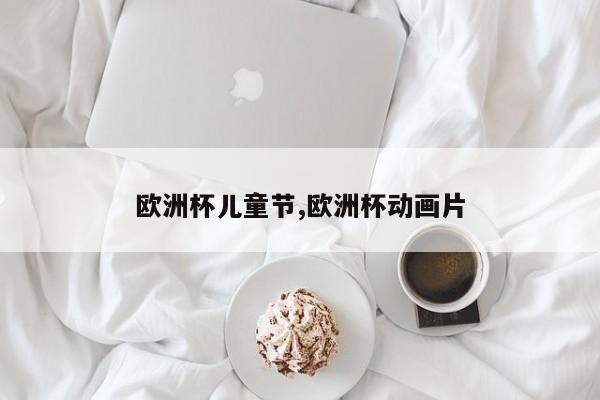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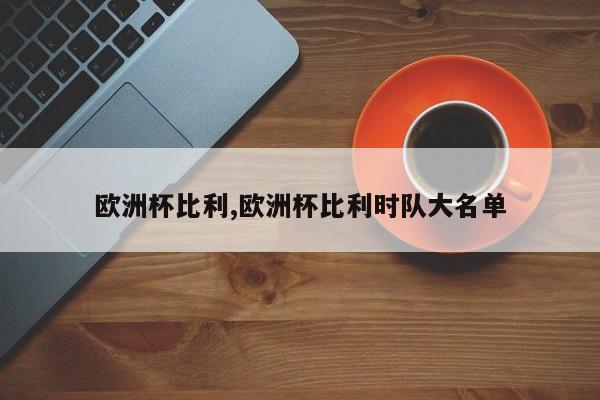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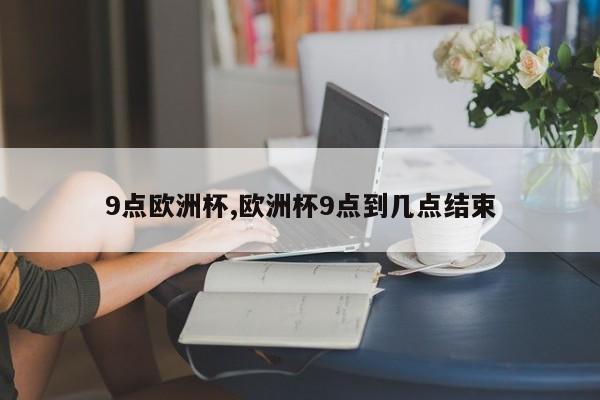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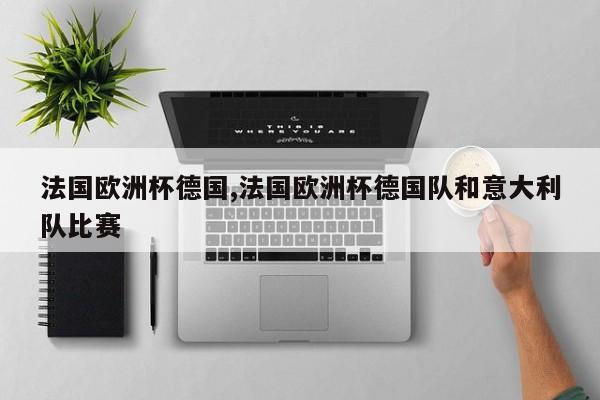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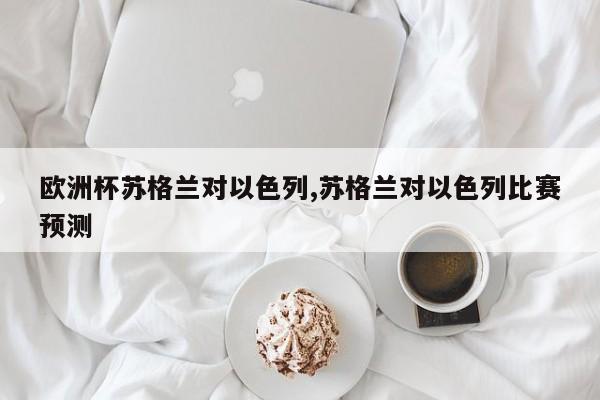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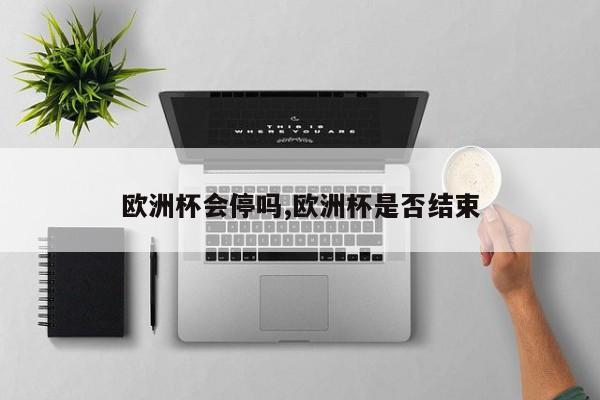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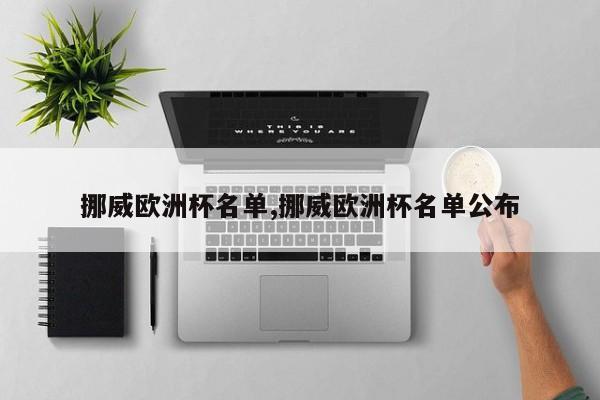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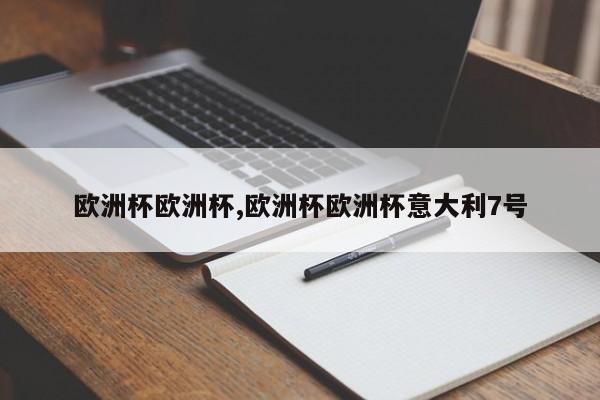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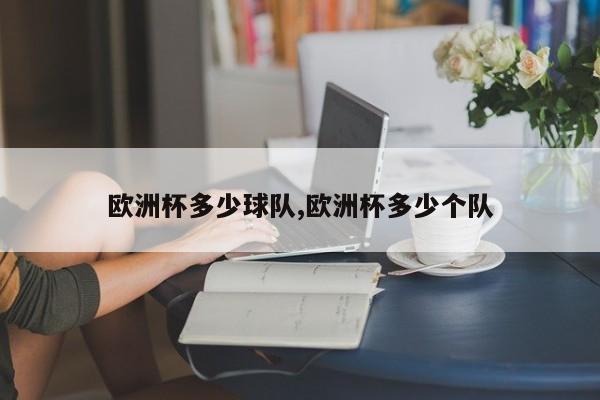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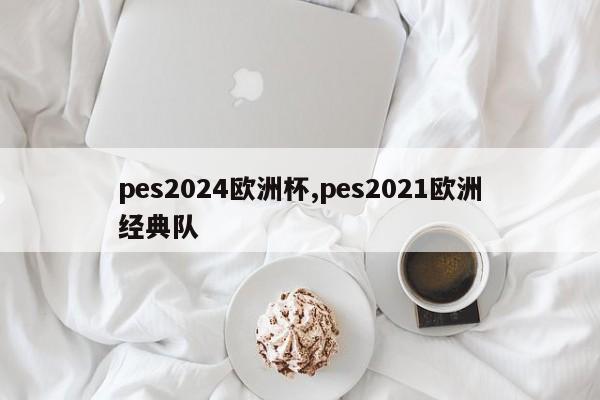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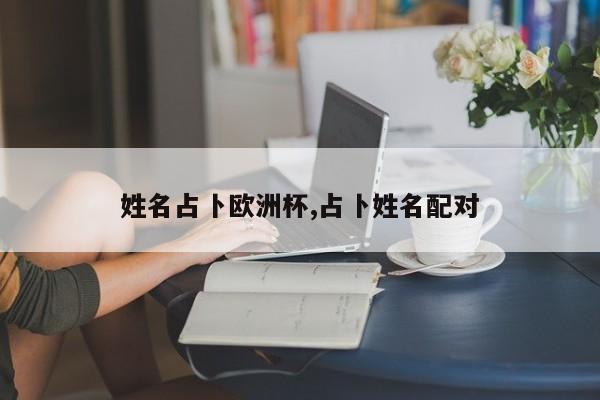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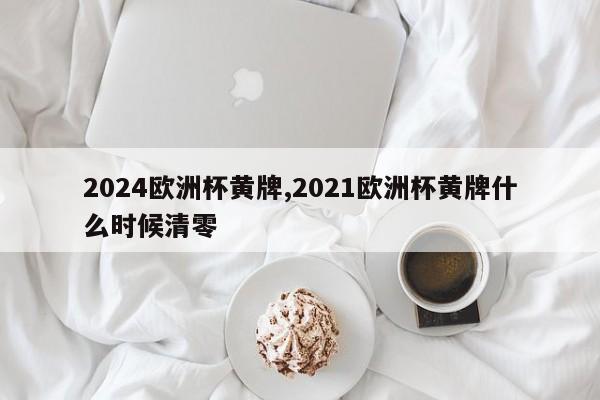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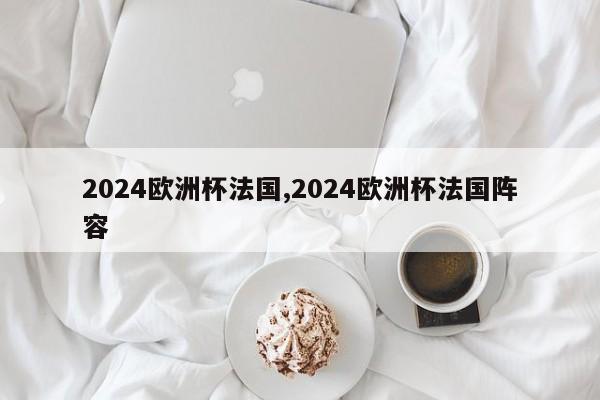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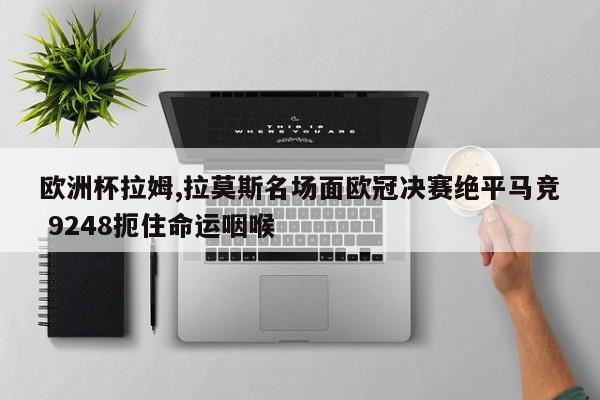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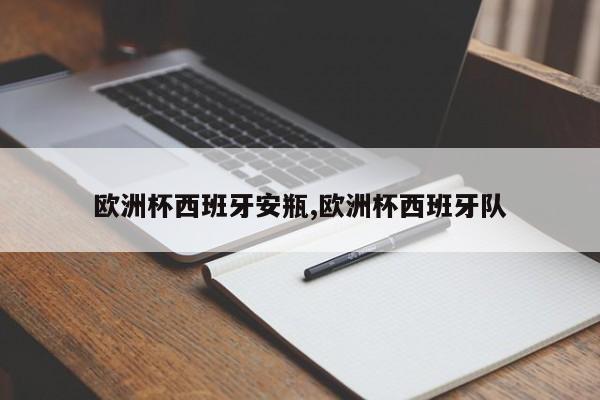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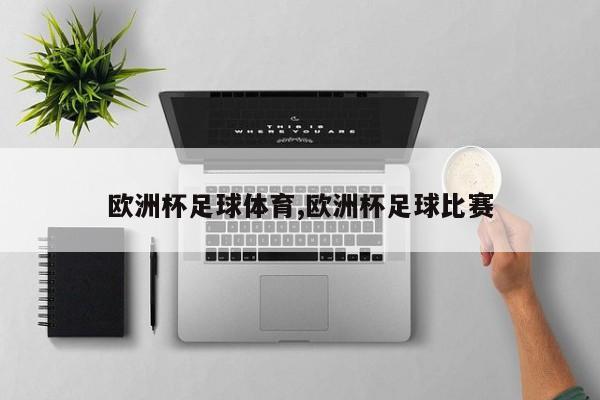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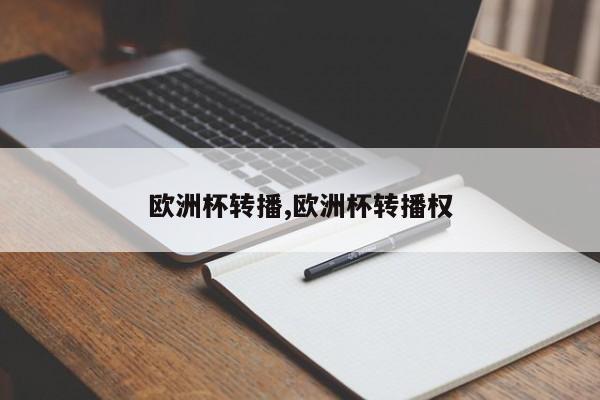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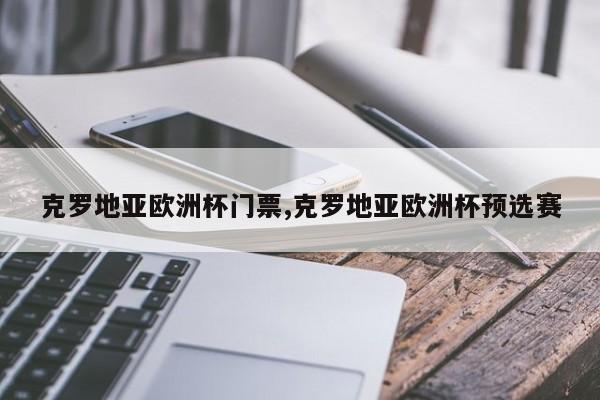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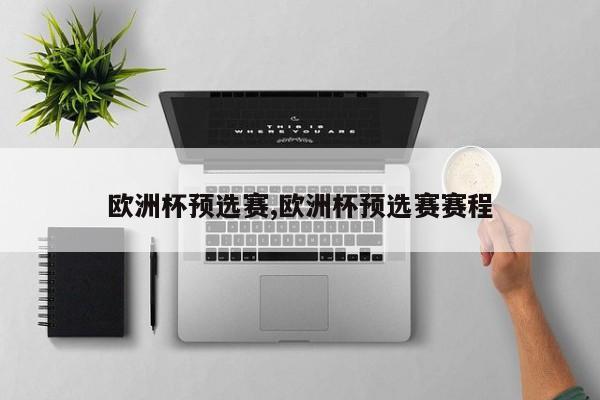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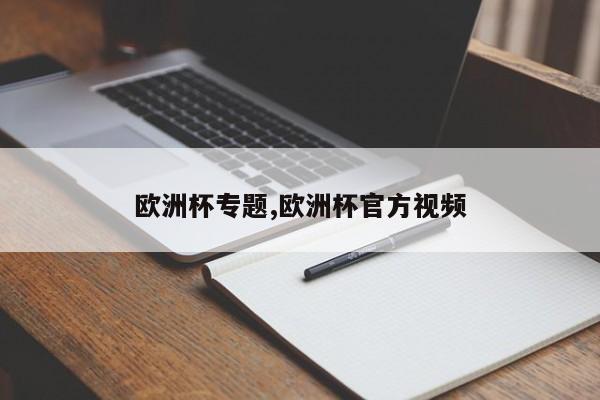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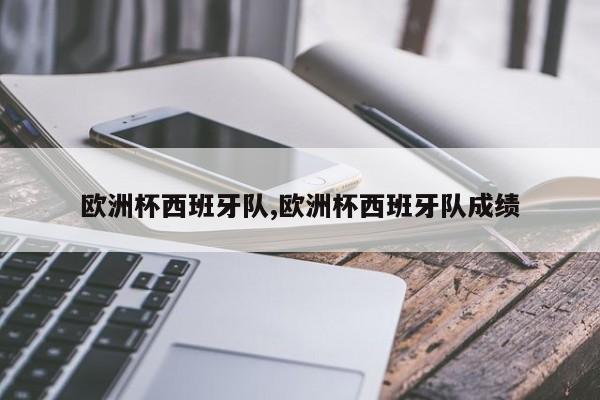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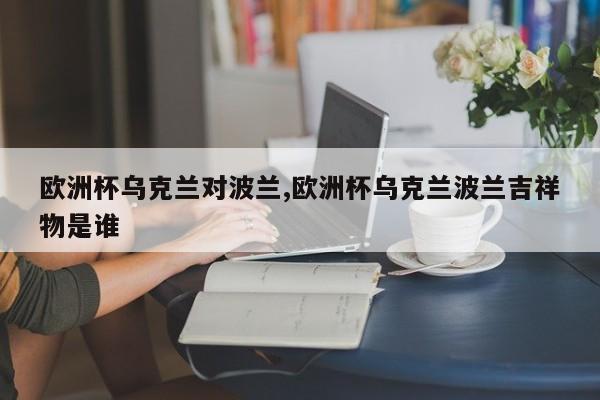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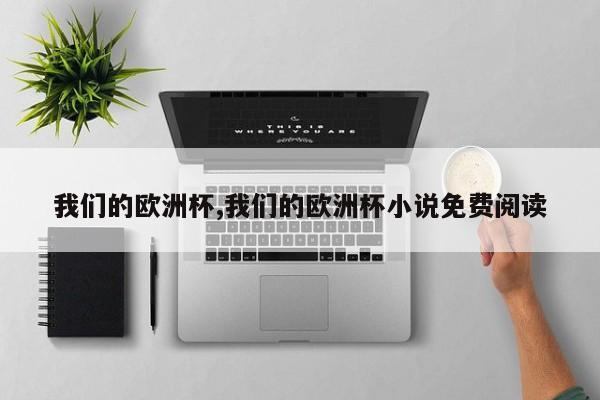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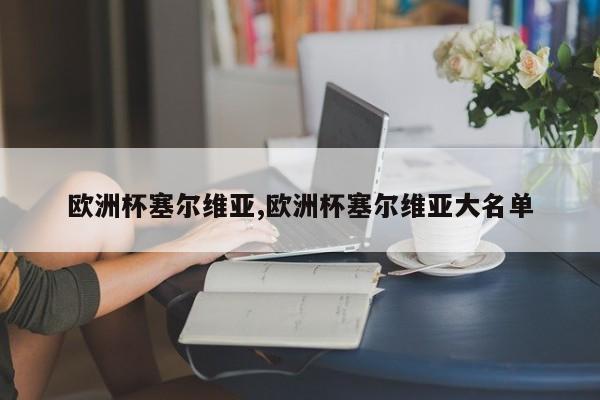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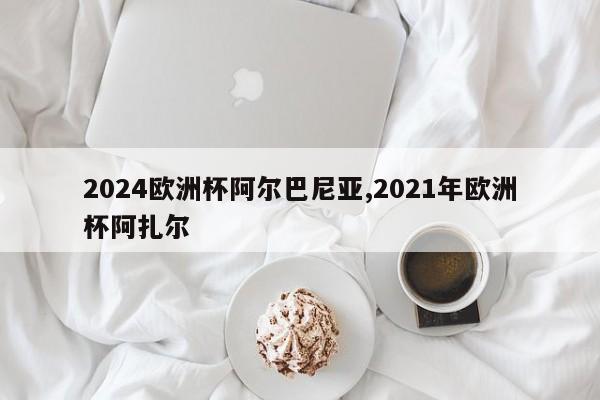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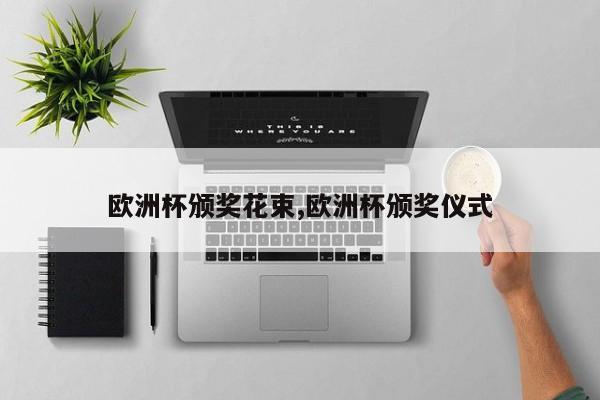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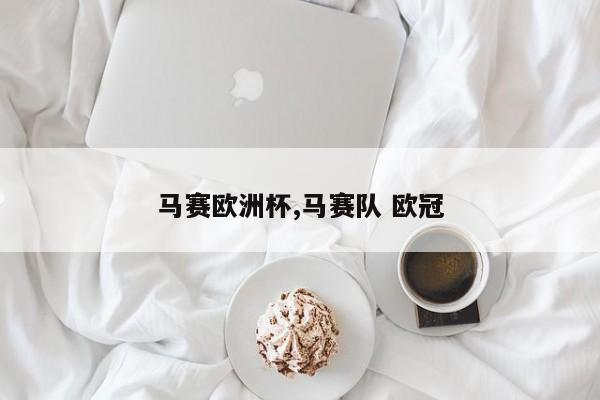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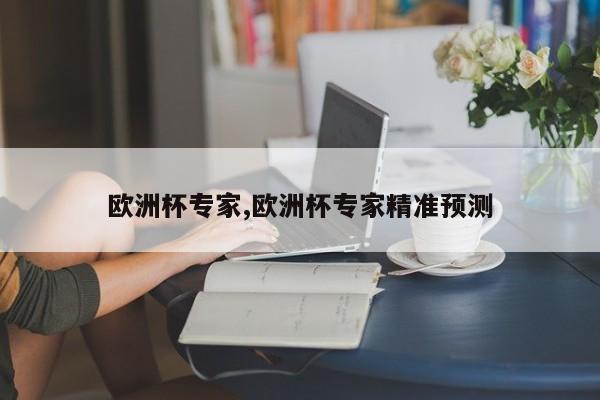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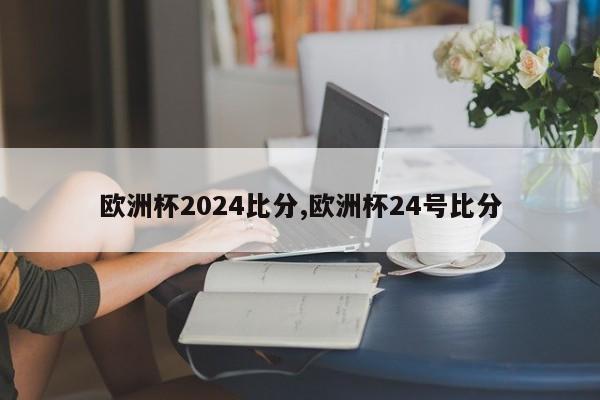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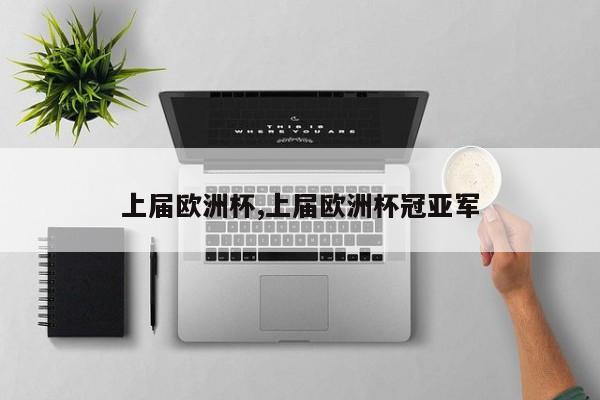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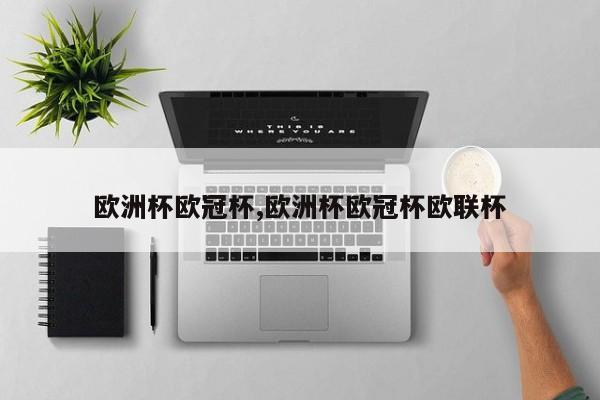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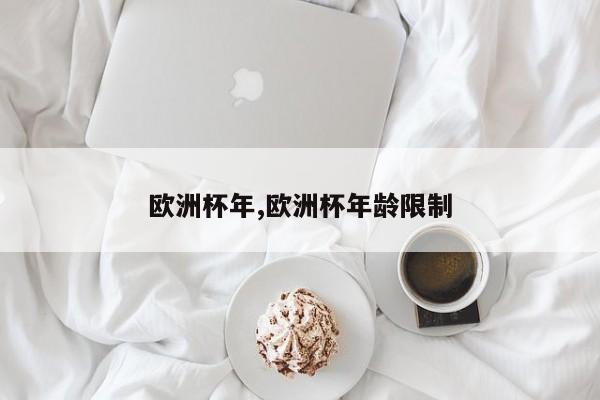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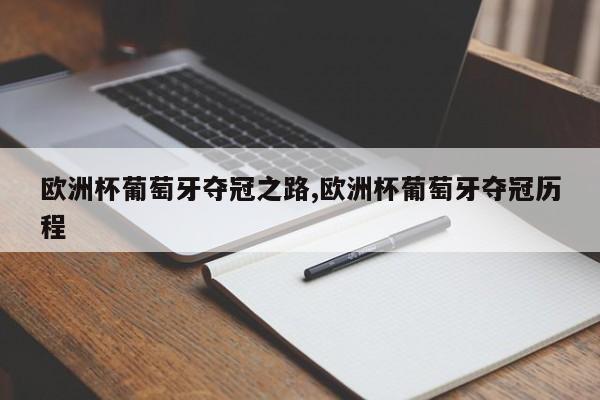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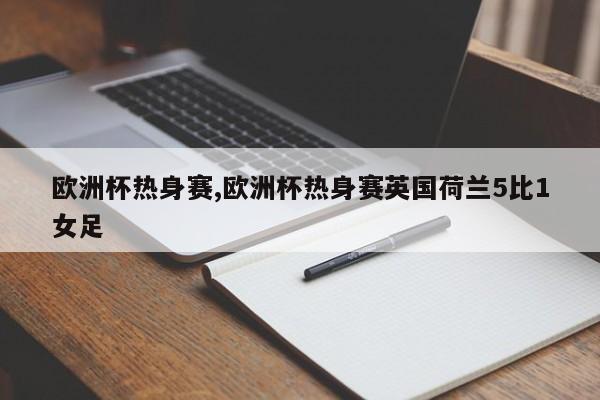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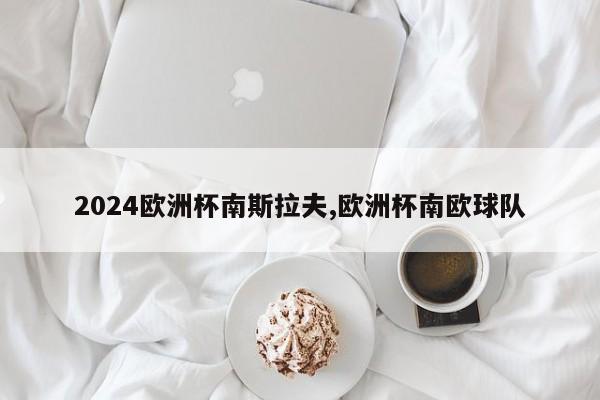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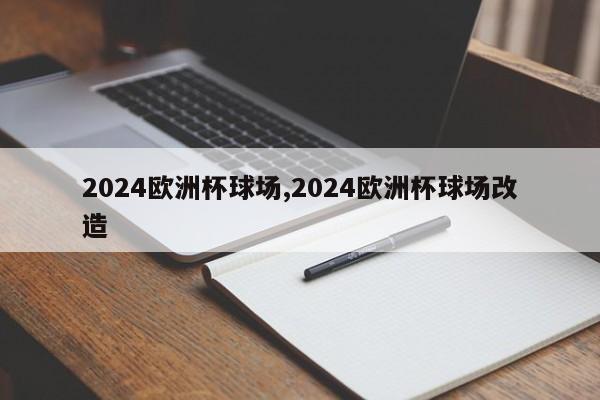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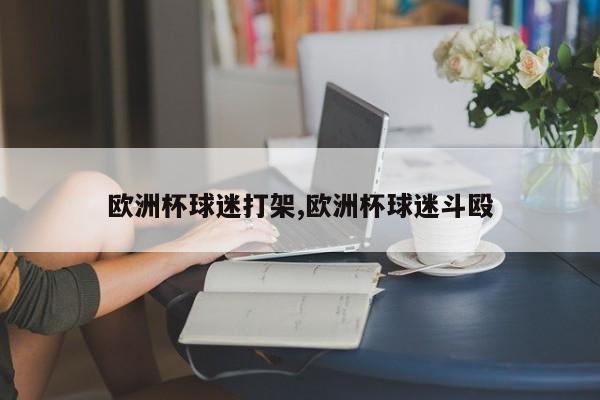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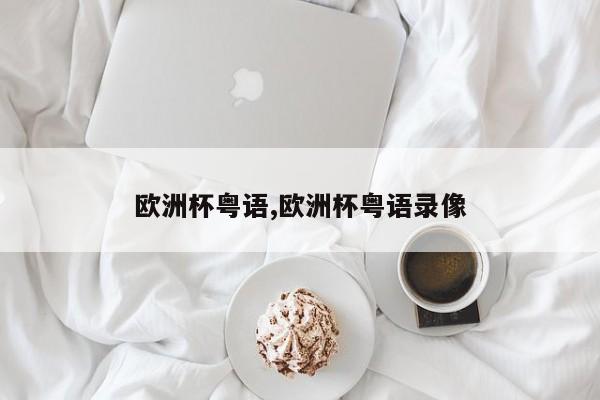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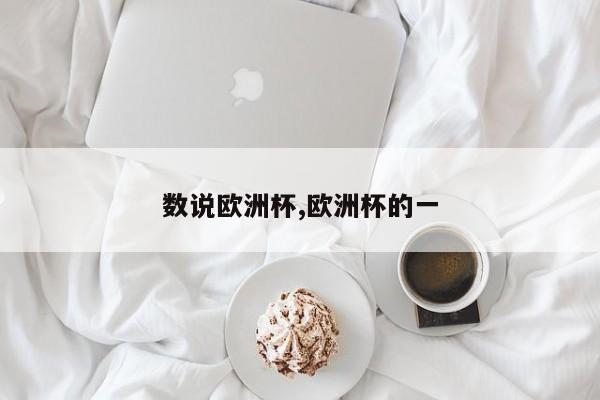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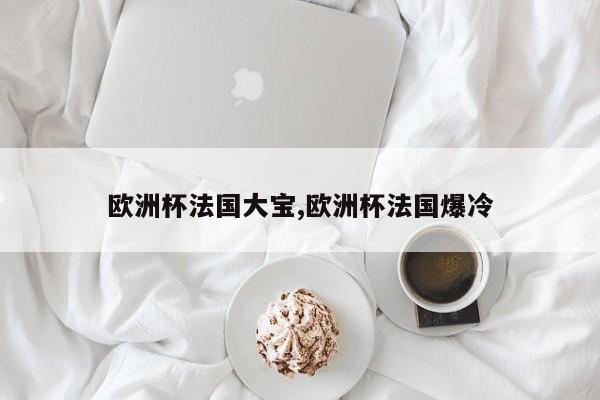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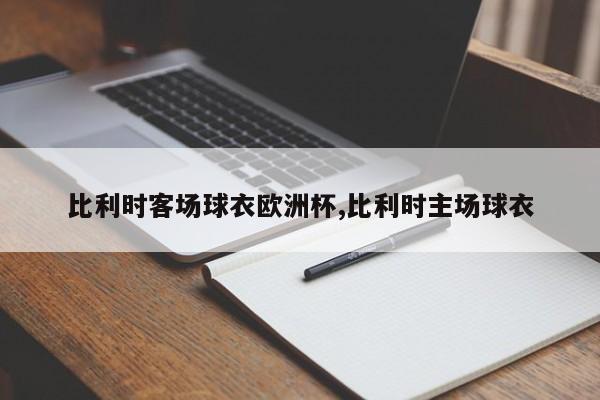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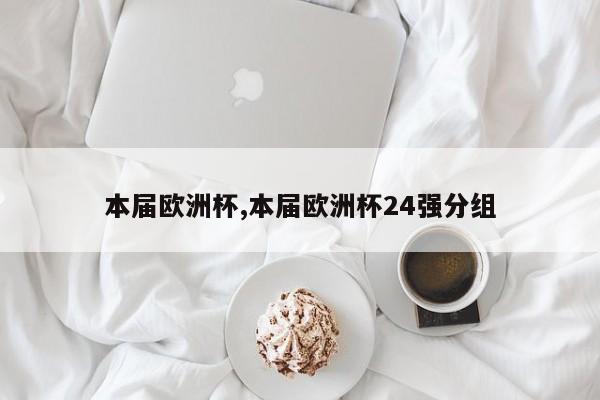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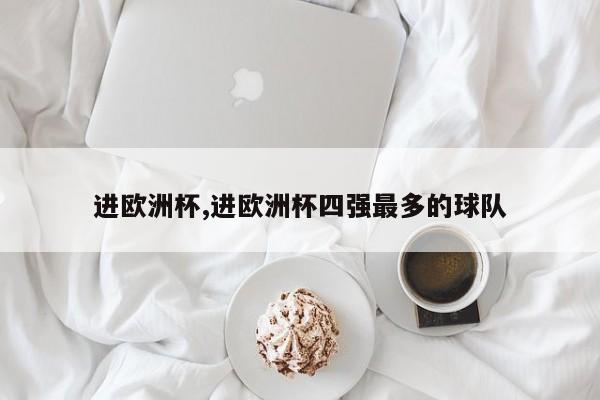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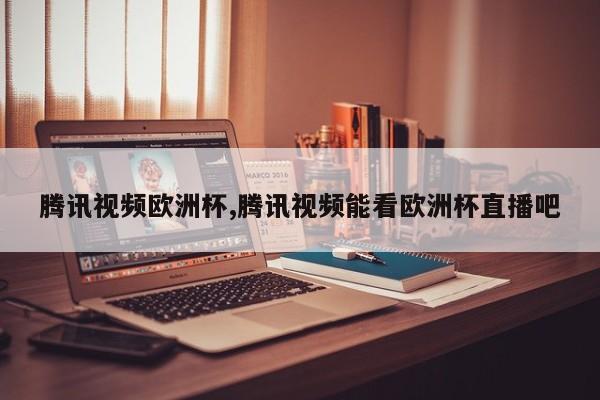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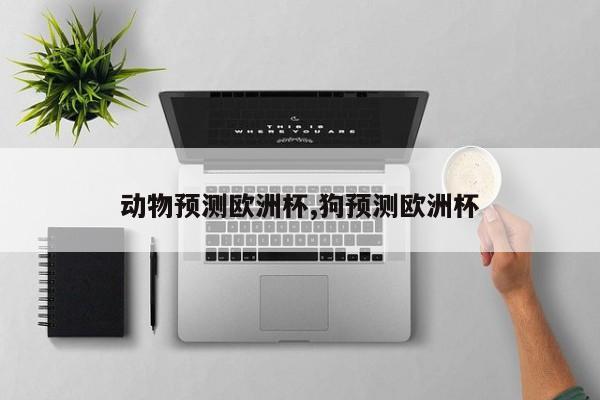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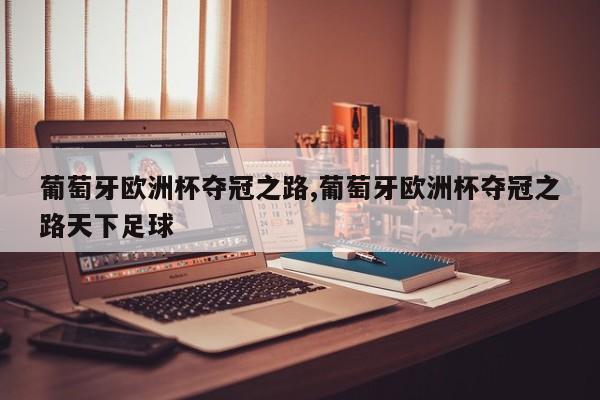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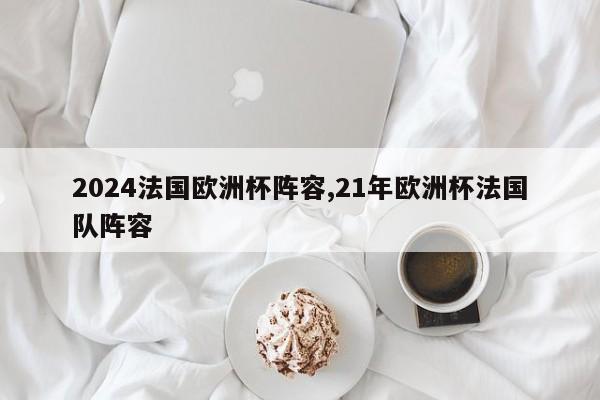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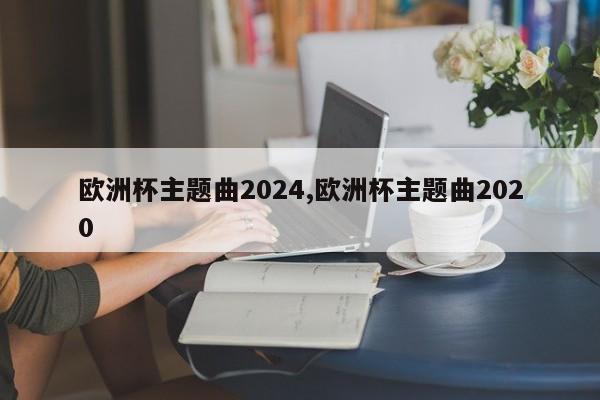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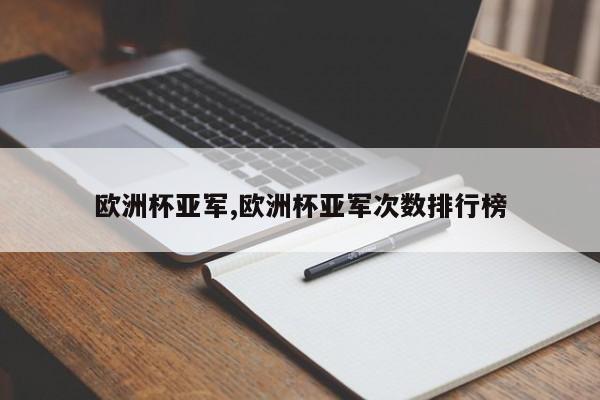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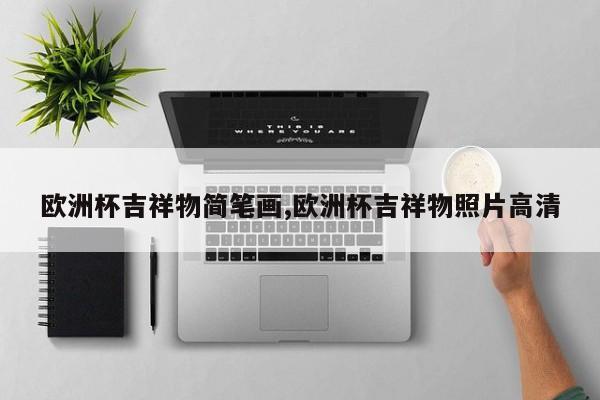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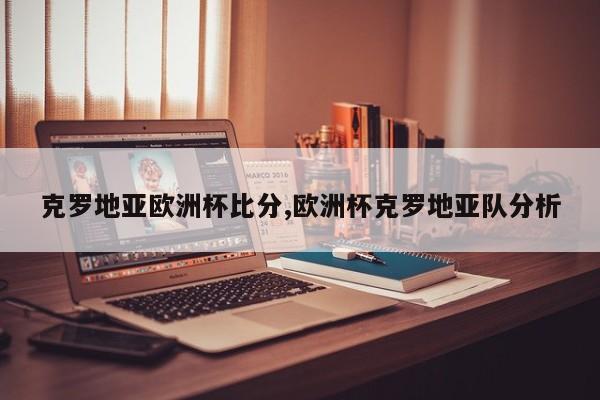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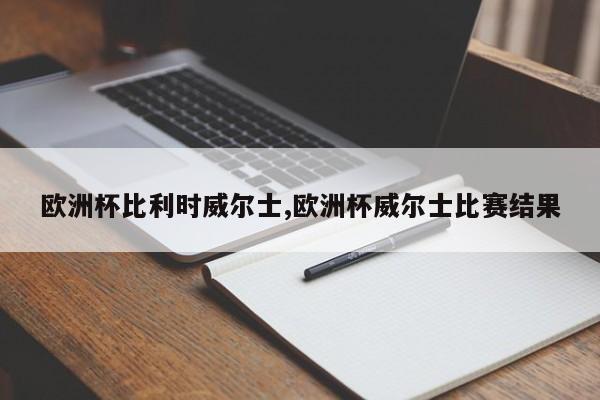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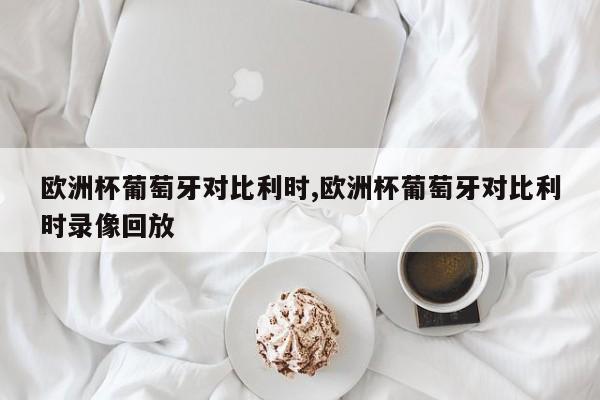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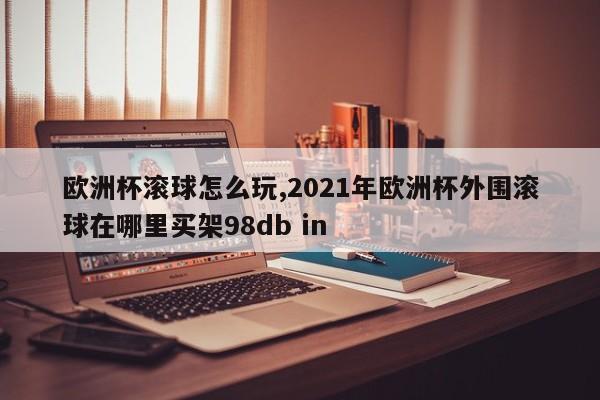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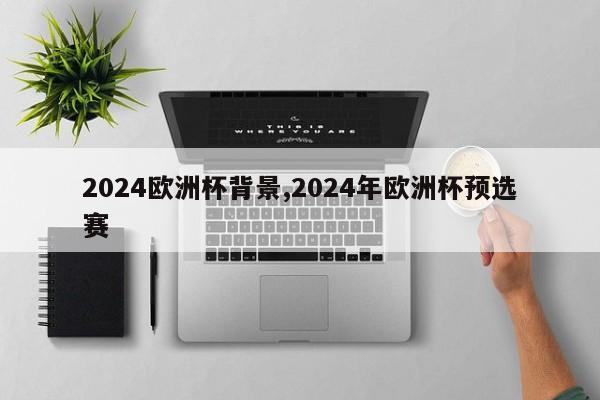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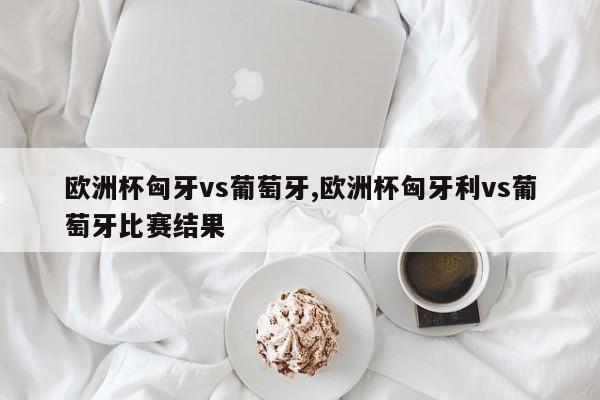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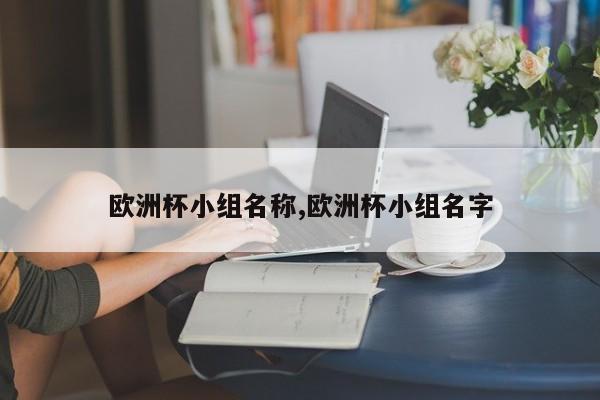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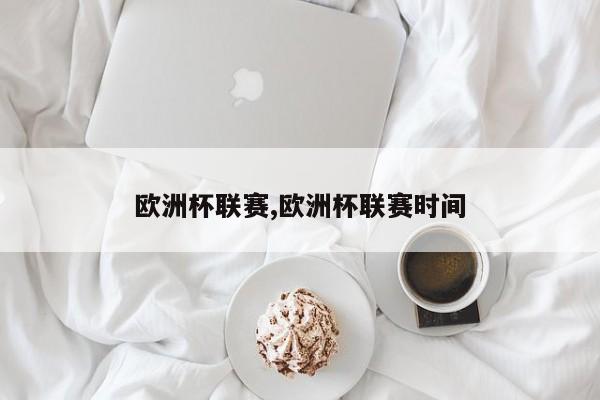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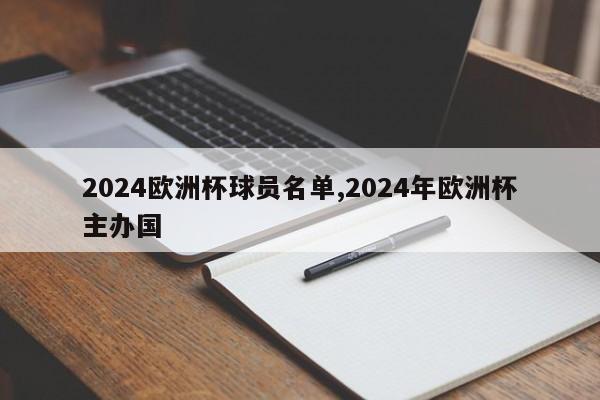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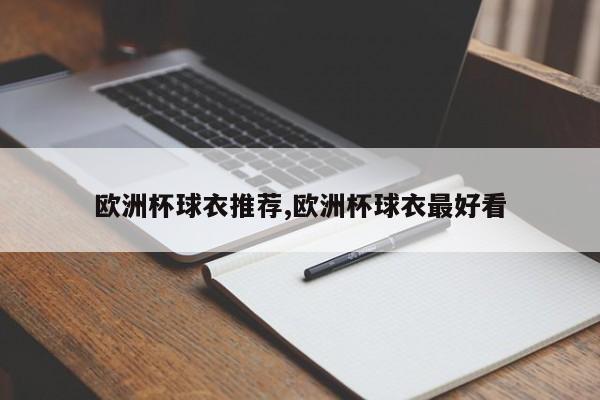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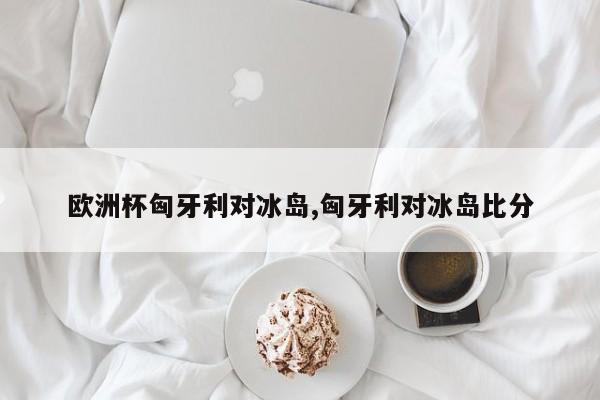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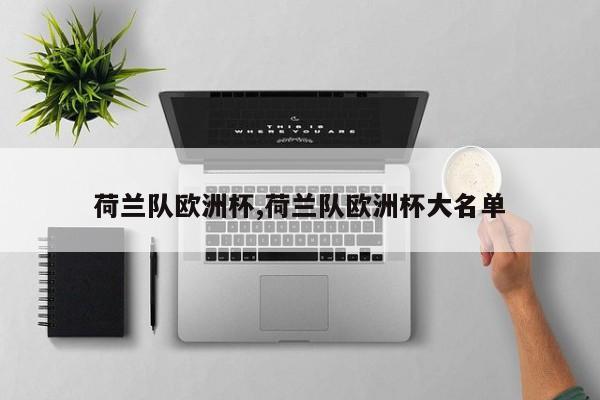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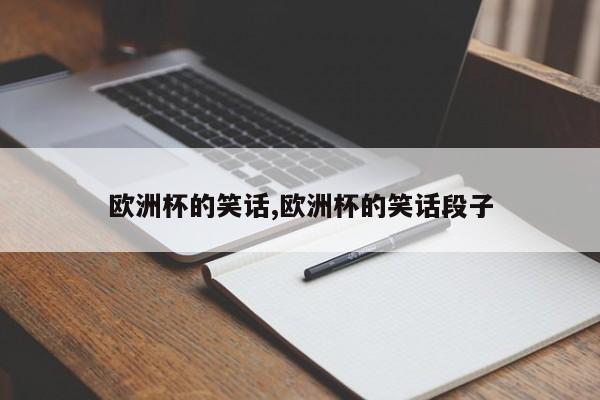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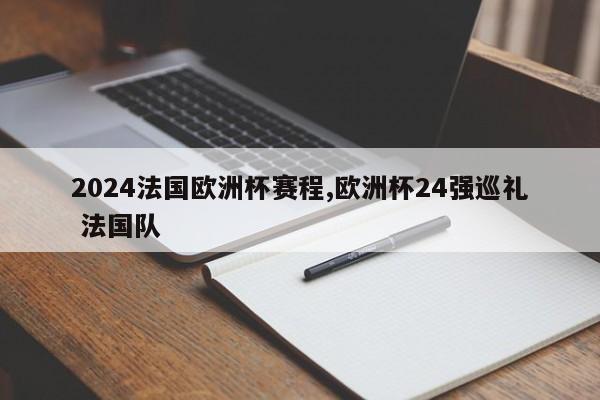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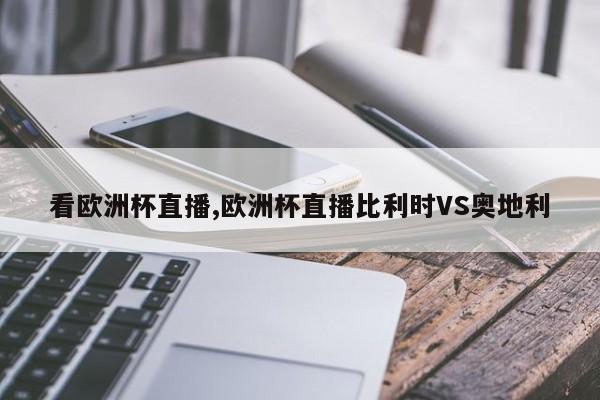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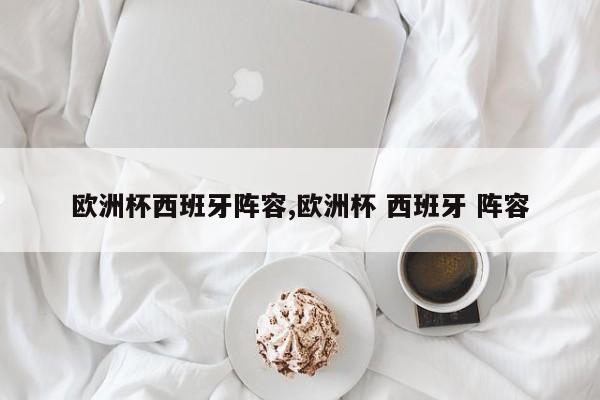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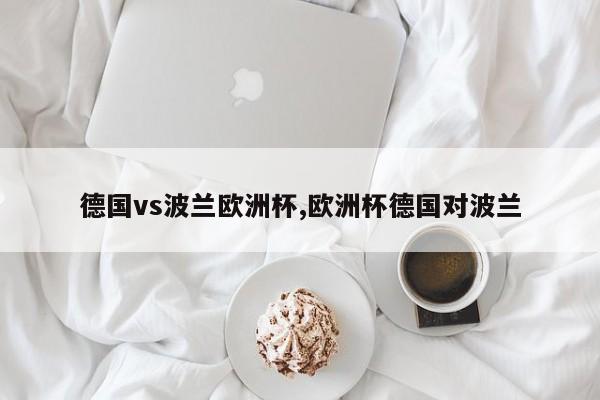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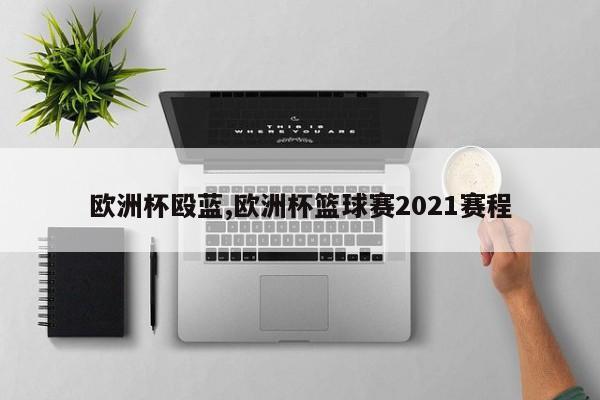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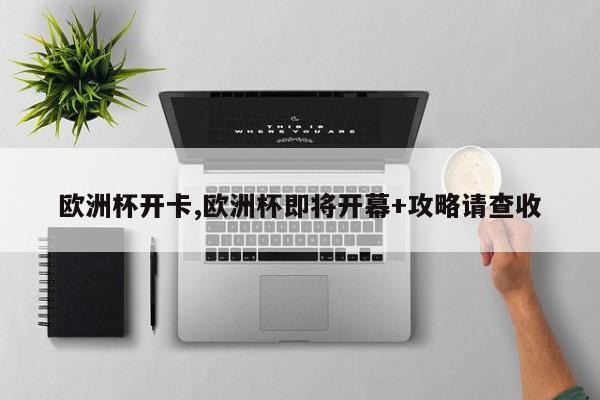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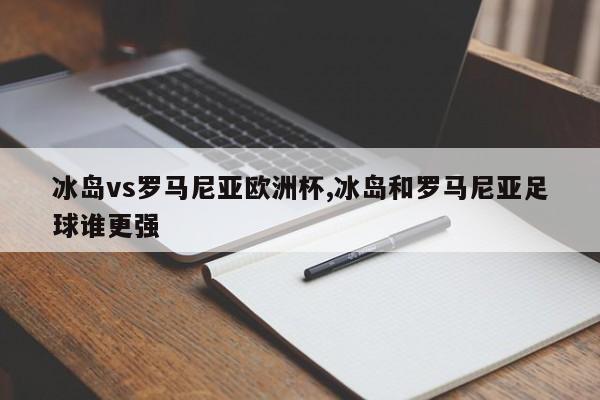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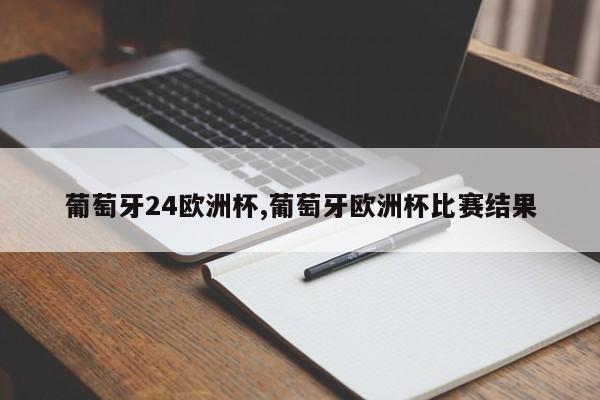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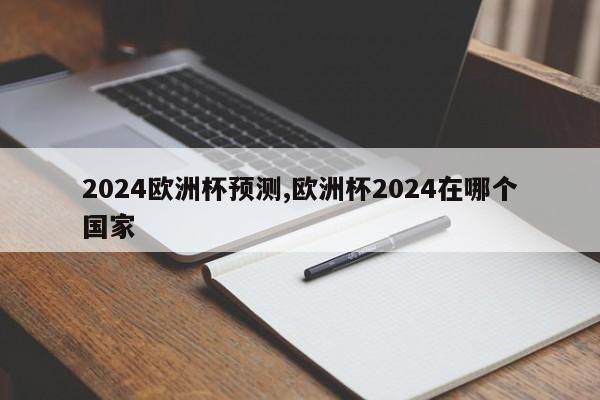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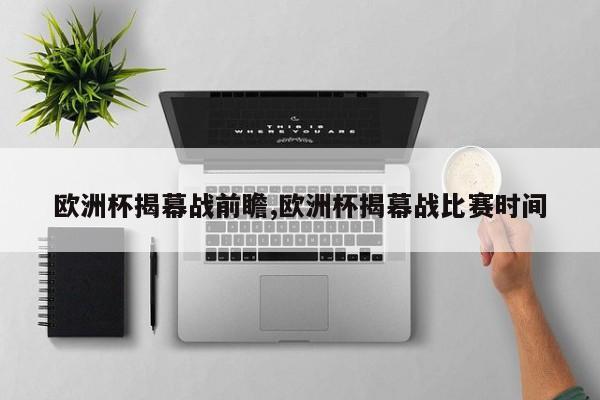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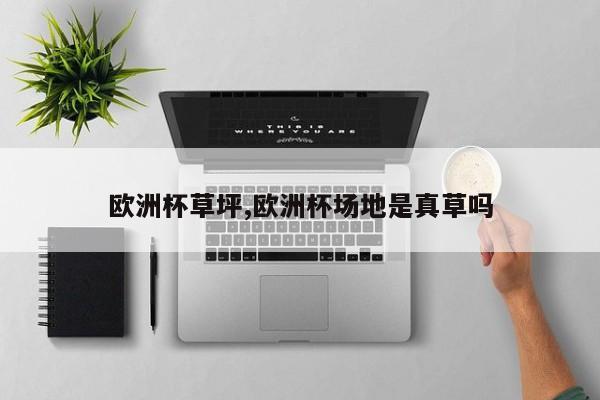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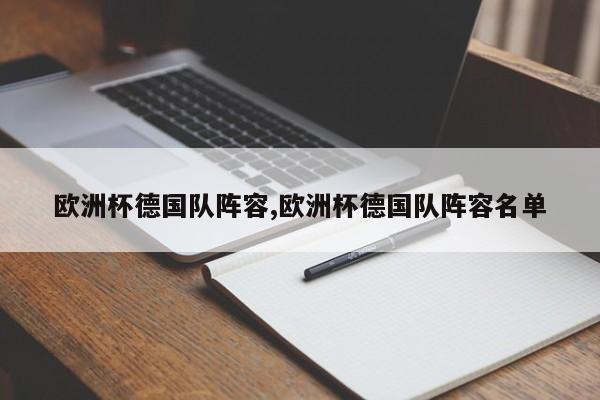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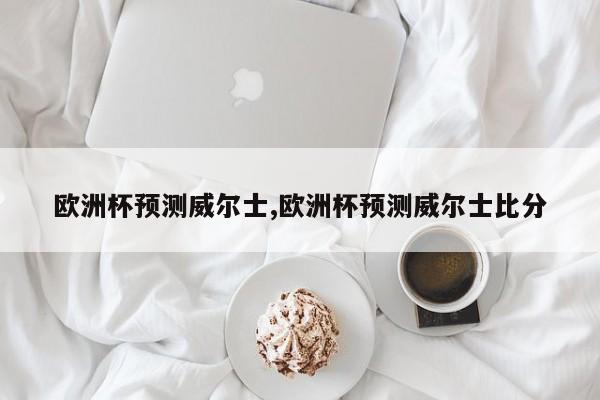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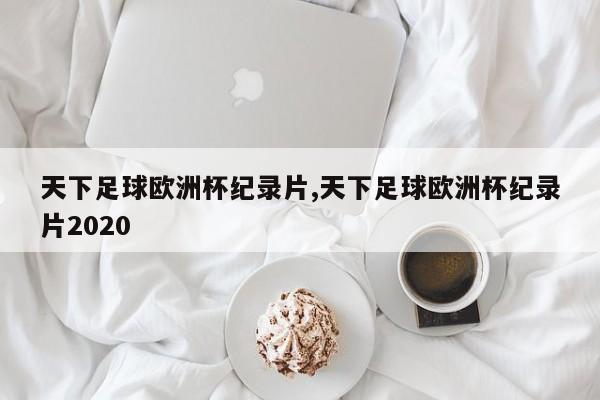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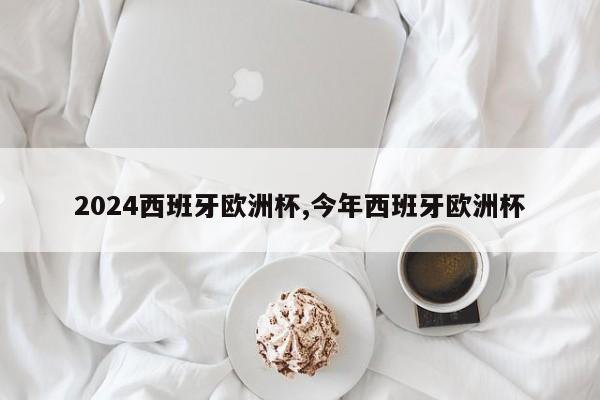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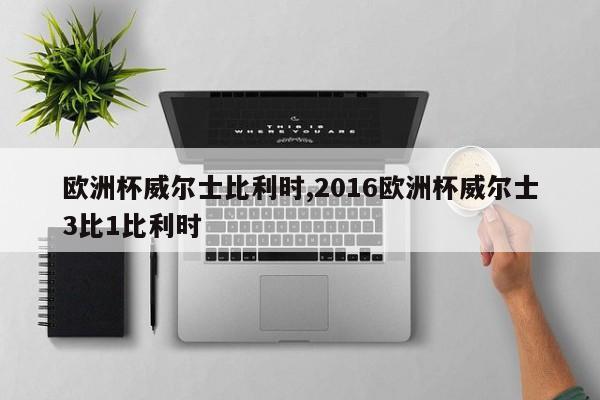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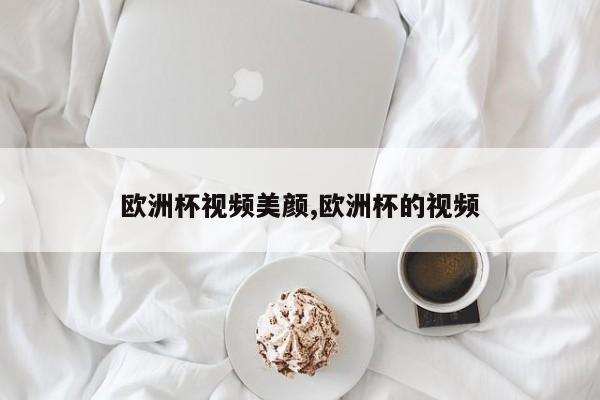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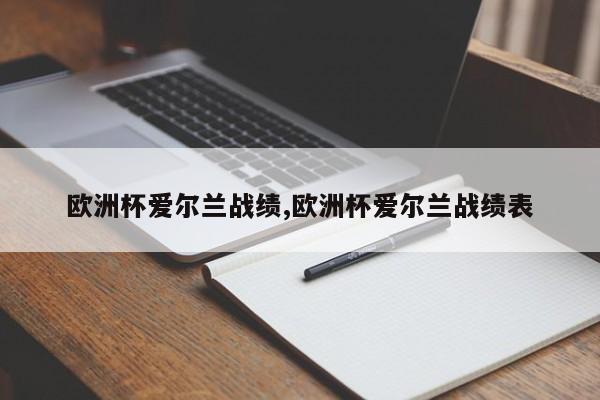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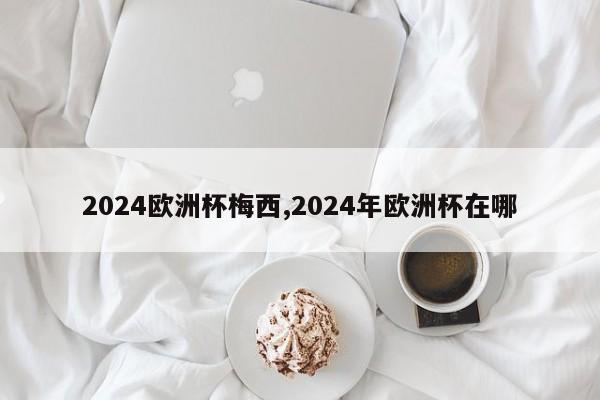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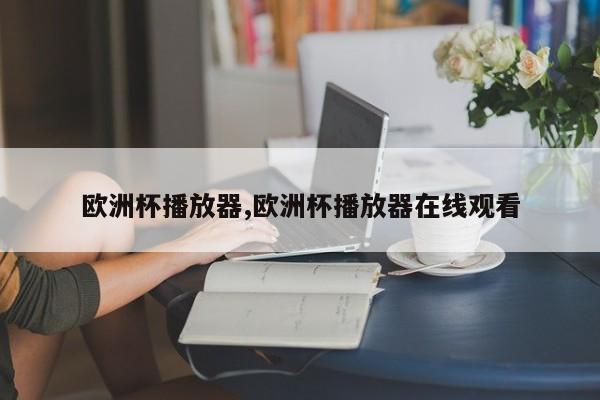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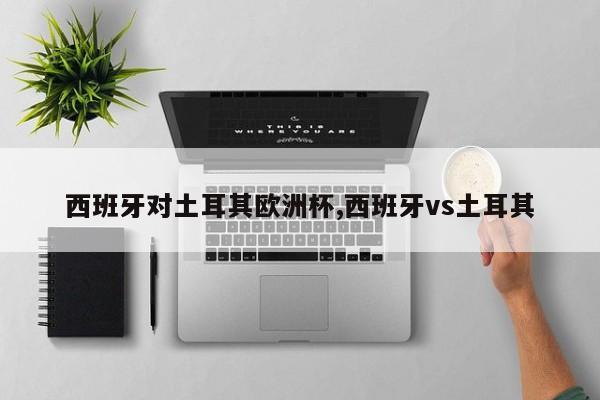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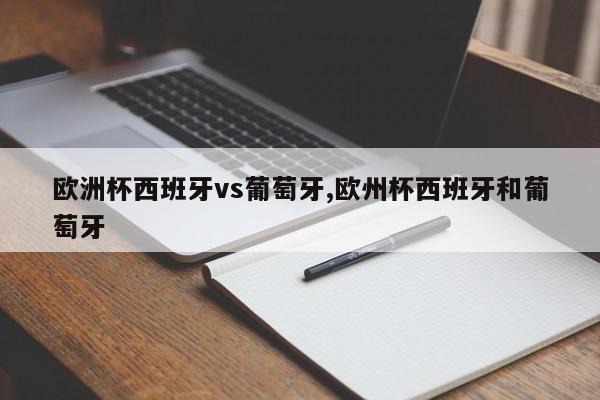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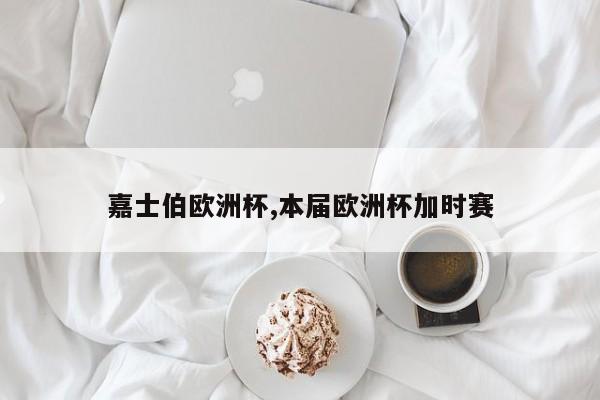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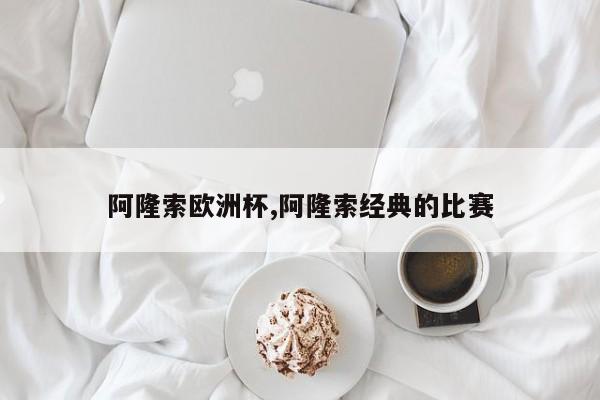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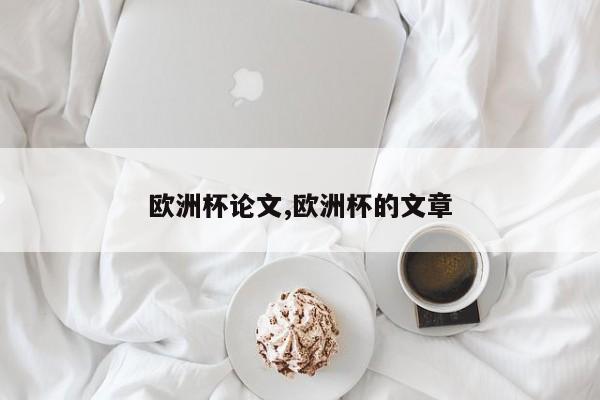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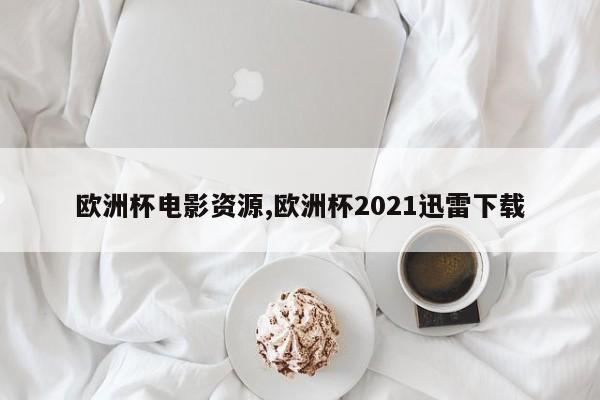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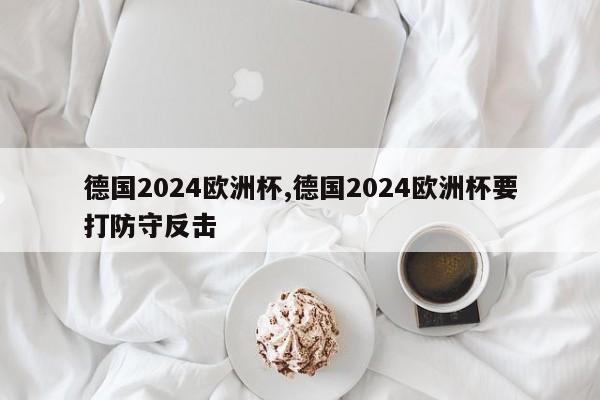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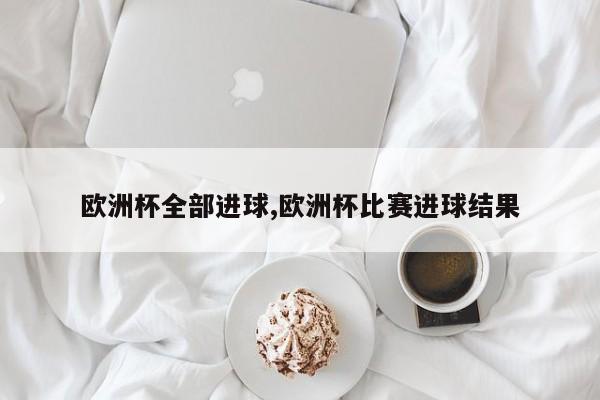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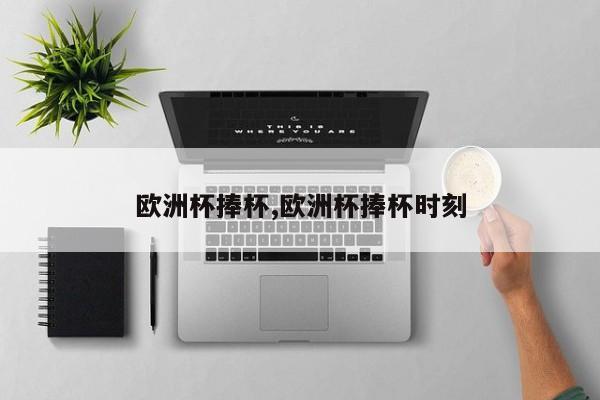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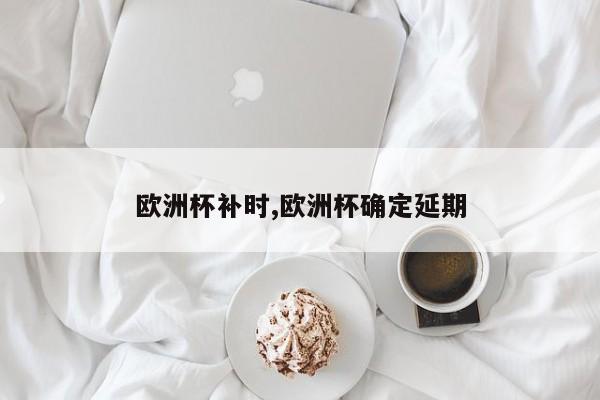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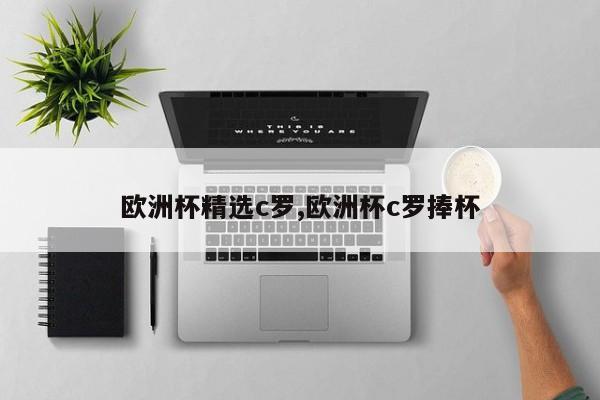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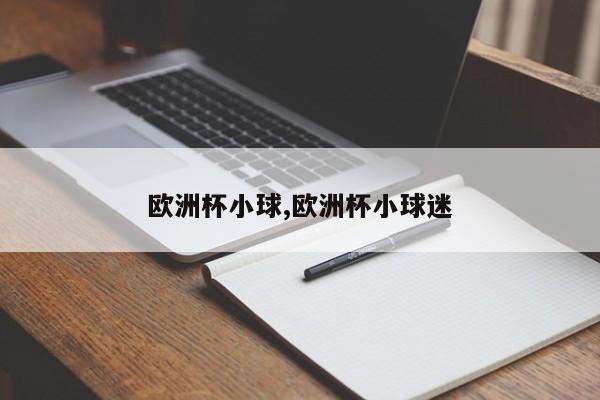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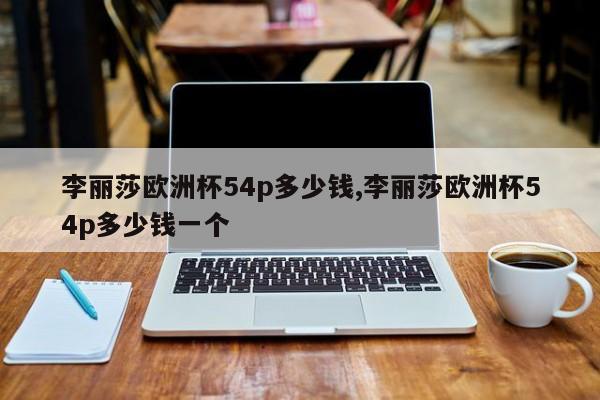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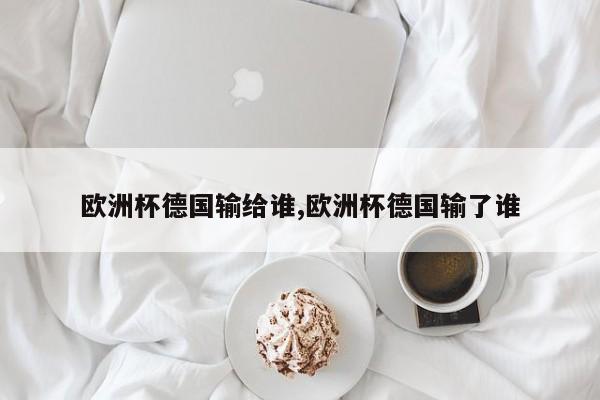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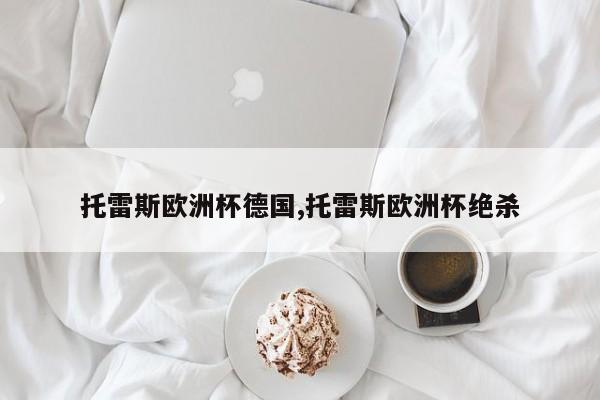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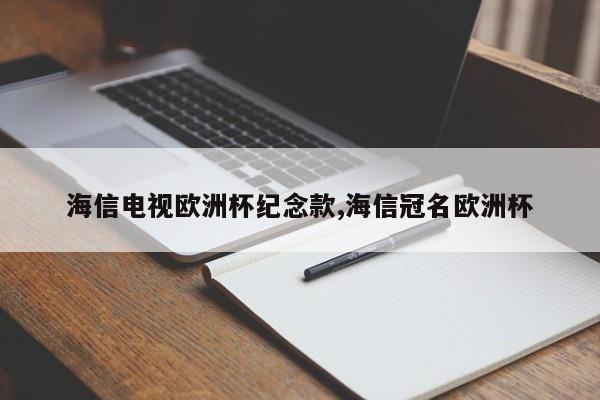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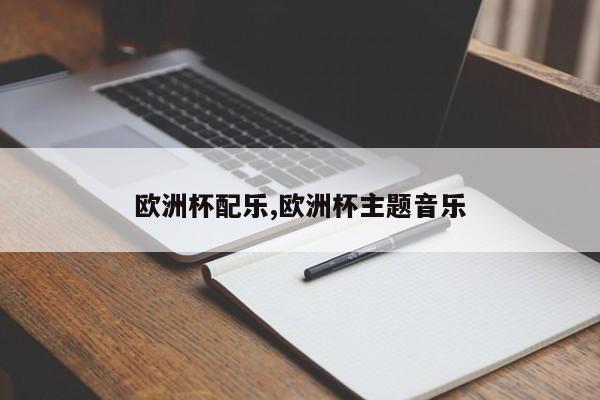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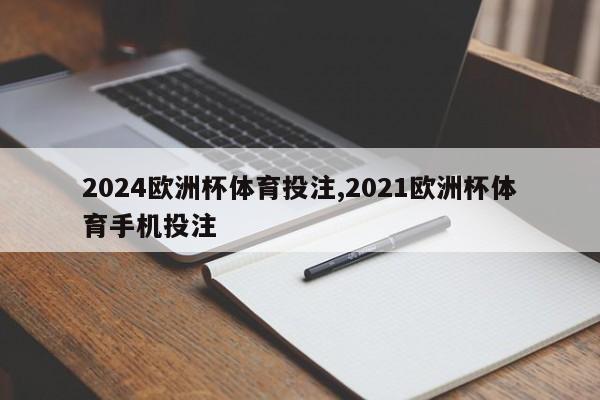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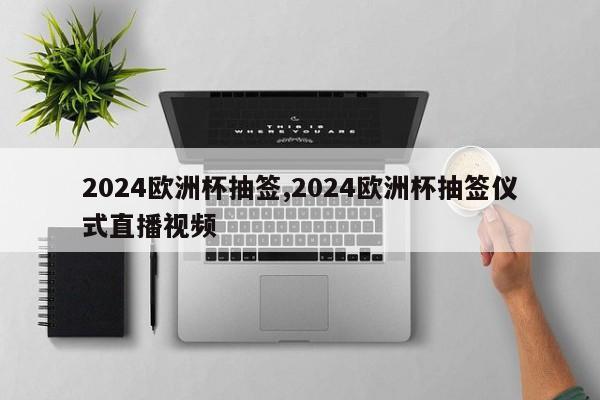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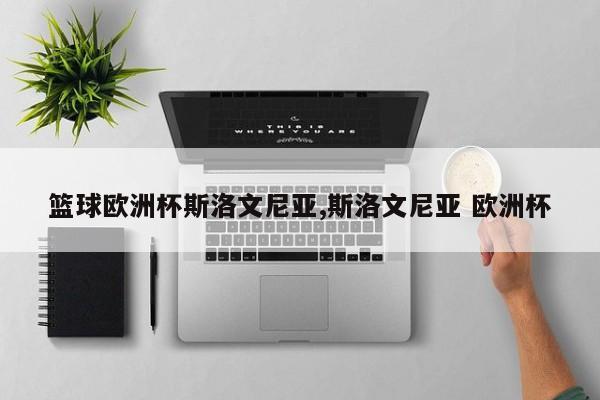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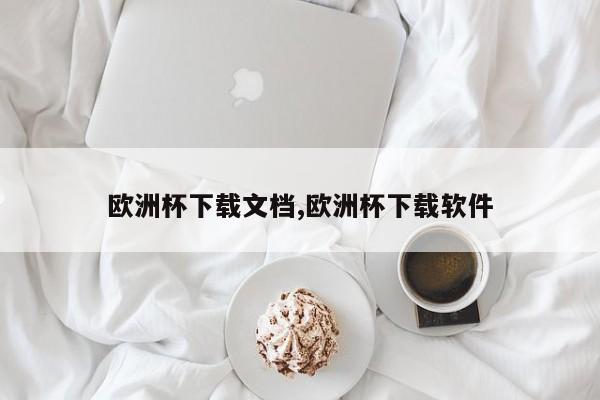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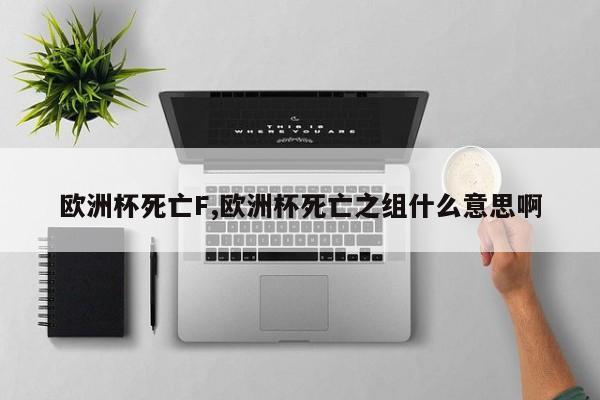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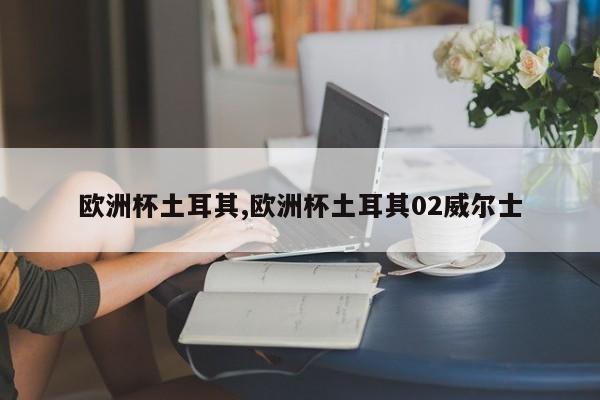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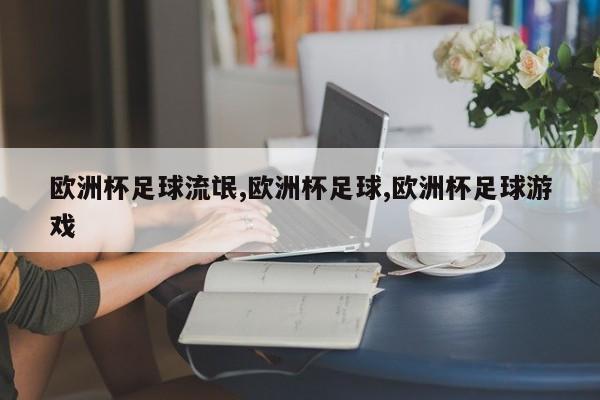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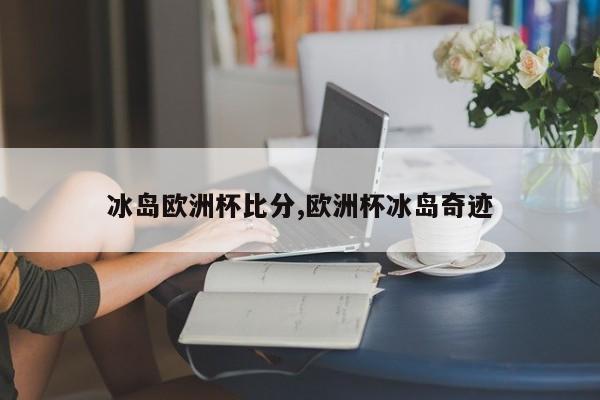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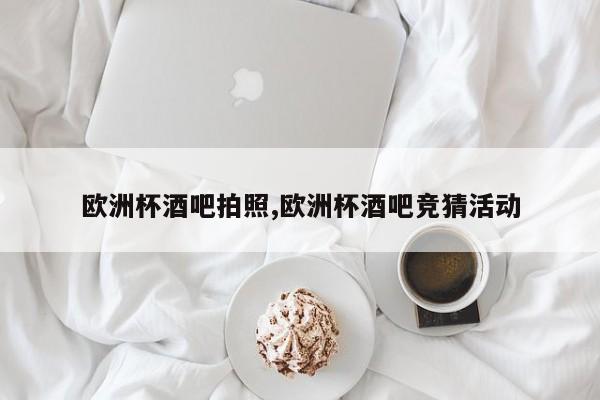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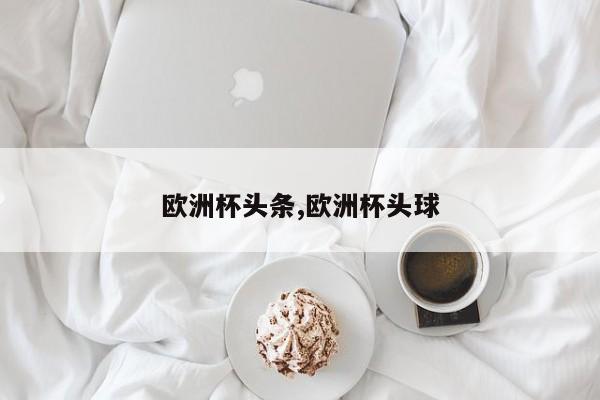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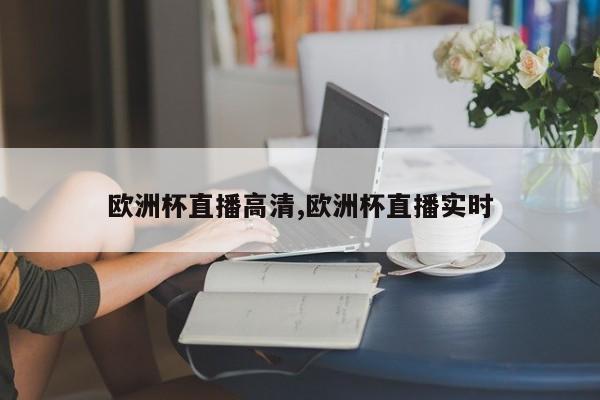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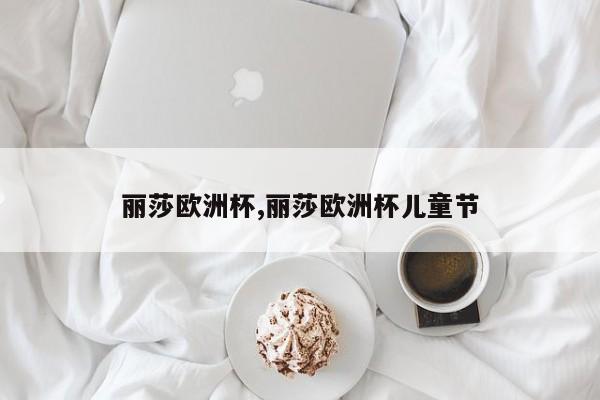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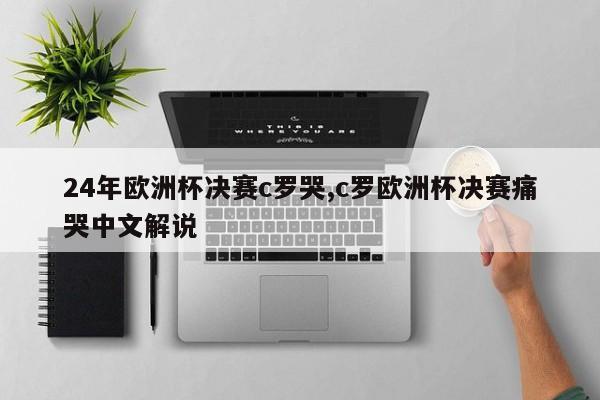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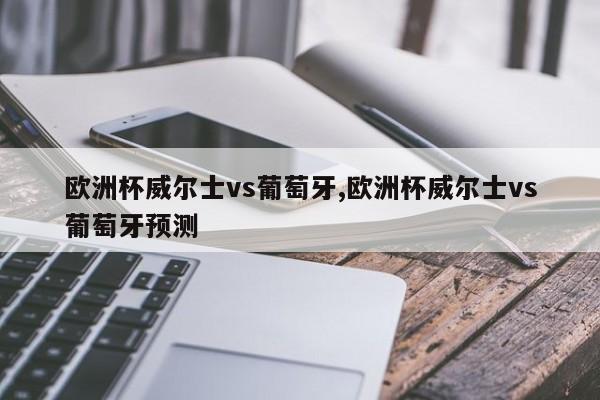





























































































































![沭阳汽车站(客运中心)时刻表skb_top();[1]](https://liaofanshequ.com/zb_users/upload/2024/02/202402121707743576251618.gif)





































































网友评论
最新评论